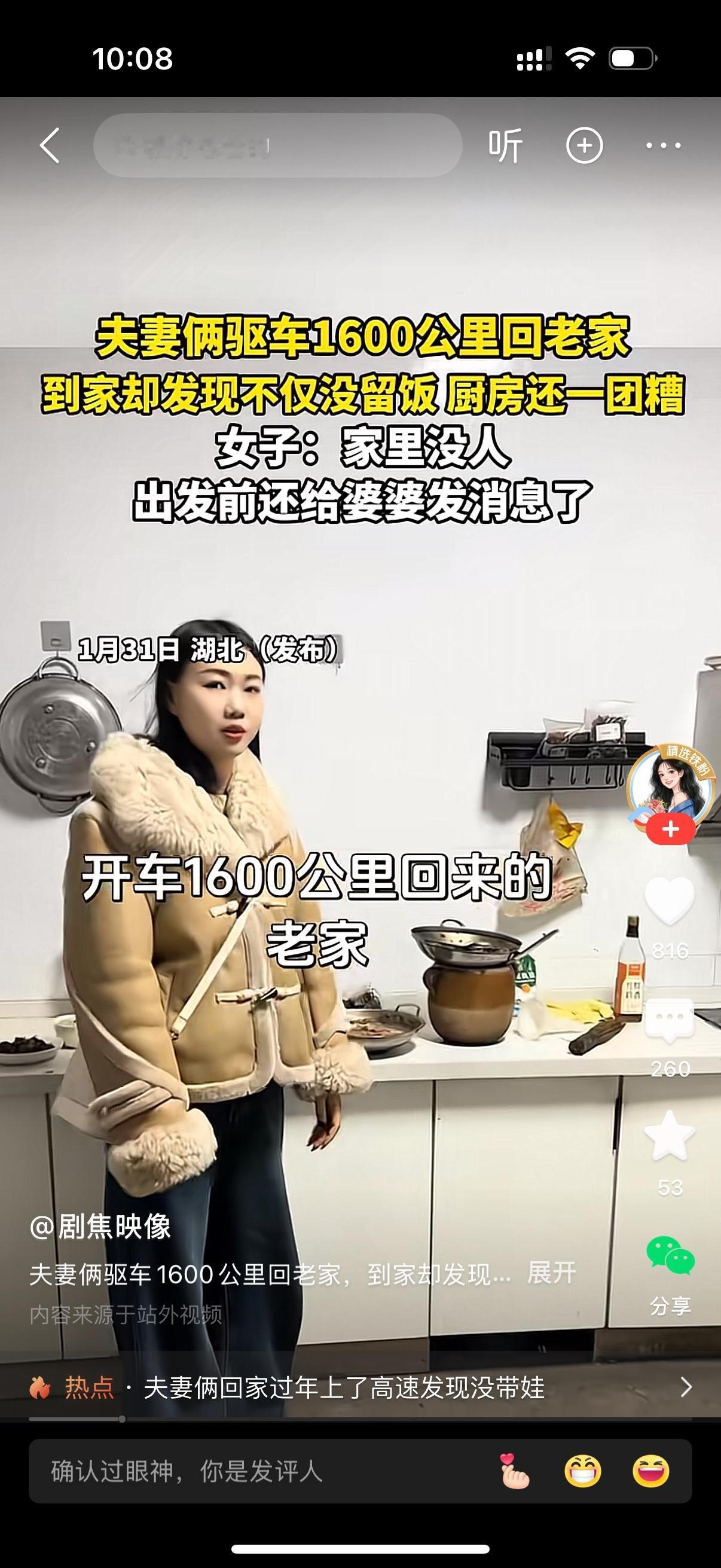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 那双在城里养得白净的手,和我们这群晒得像黑炭的手,格格不入。 他说自己是记者,眼睛里却放着饿狼一样的光,对着电话那头喊:“全是宝藏! 我必须留下! ” 宝藏? 晾衣服的手停在半空,白菊的眼神瞬间就冷了。 我和老韩对视一眼,心里门儿清——县长派来盯梢的。 这地方,除了风沙和我们这几条糙命,哪来的宝藏? 真正的宝藏,是不能写在纸上的。 是我们夜里听到的枪声,是雪地里那串孤零零的脚印,是白菊夜里偷偷抹的眼泪。 老韩把烟屁股摁灭在墙上,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这哥们儿要是真留下了,我这‘失足青年’的先进事迹,怕是要上报纸了。 ” 白菊头也不抬,甩过来一句:“有这个可能。 你是典型。 ” 一阵哄笑。 笑声粗粝,像被风吹了千百遍的石头。 我们的世界,外人永远看不懂。 他们带着猎奇的眼光,想挖走点什么当成勋章。 而我们,只是想让这片土地,和我们自己,都好好活着。 幽默,是我们唯一能穿在身上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