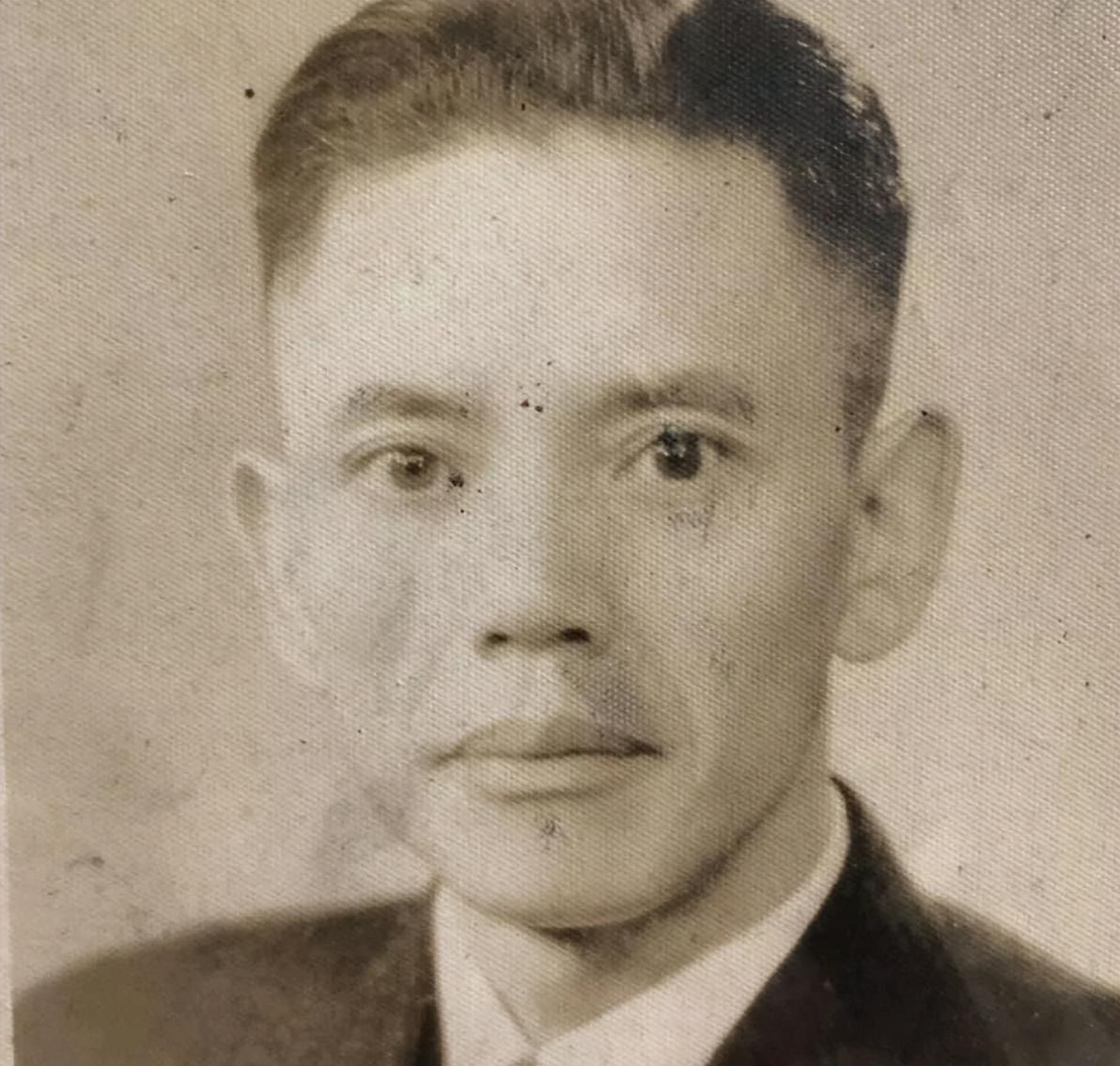1975年,周养浩被特赦,重获自由后,国家允许周养浩去任何地方,周养浩提出:“我想去台湾投奔老蒋!”谁知周养浩刚出发,蒋介石就死了! 1975年3月,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养浩捏着特赦通知书的手微微发颤。 纸上“准予释放”四个字,像块烙铁烫在掌心里。 管教干部递来三张表格:“留京、返乡、经香港去台湾或出国,你选。” 他没抬头,笔尖在“赴台”栏重重一顿。 “你真要去?” 干部皱眉,“政府给你安排工作,安顿得好好的……” “我认老蒋。” 周养浩把笔一撂,“二十年前他给过我前程,现在该我还债了。” 刚进功德林时,周养浩简直是块捂不热的铁。 同监舍的沈醉总说:“这老哥心里揣着本账,算得比谁都精。” 审讯时他搬出《刑法》条文,把问话变成法庭辩论。 劳动时故意慢半拍,等别人干完活再“帮忙”收尾。 有次徐远举脾气上来要揍他,他眼皮都不抬:“《日内瓦公约》第几条来着?虐待战俘要追责的。” 可谁也没想到,这“笑面虎”会在1960年突然变了个人。 那天沈醉被特赦,临走前夜拍着他床板说:“好自为之。” 第二天,周养浩就找干部要了本《新华字典》,把上海话“侬”改成“你”,把“阿拉”换成“我们”。 劳动时他抢着挑粪桶,别人休息他擦地板,积年油垢擦得能照见人影。 1975年4月,周养浩站在罗湖口岸回头望了眼北方。 云层压得像口没掀开的锅盖,他攥紧手里的赴台批文,心里盘算着到台湾后的日子。 或许能当个顾问,或许能领份退休金,总比在大陆“吃闲饭”强。 可他刚到香港,收音机就炸了,蒋介石死了。 那晚他伏在唐楼的小桌前誊写自传,他盯着“领袖英明”四个字看了半小时,最后划掉改成“时局变迁”。 “老周,节哀。” 旧部捎来蒋经国的回电,“先父新丧,百务待理,容后续商。” 十二个字像盆冰水浇透了他。 接下来的日子,他成了北角街头的“怪人”。 每天三趟去邮局查收台湾电报,风雨无阻。 有次台风天,他撑伞在泥水里摔跤,怀里的电报稿撒了一地。 他趴在地上一张张捡,像捡救命稻草。 “周先生,别等了。” 邮差劝他,“台湾那边早把你忘了。” 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我等的是自己。” 而转机来自美国。 女儿写信说外孙女生病,想见外公。 周养浩捏着信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改去美国探亲。 工作人员看着他的行李箱叹气:“想去就去吧,大陆的门永远开着。” 离港前夜,他烧了写了一半的回忆录。 “原来我这一辈子,就剩这点念想了。” 飞机掠过太平洋时,他第一次感到轻松。 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出口,外孙女扑进他怀里喊“外公”,可他喉咙像堵了团棉花。 女儿后来发现,他口袋里还揣着没寄出的《赴台申请书》。 在美国的日子像杯凉白开。 他搬进马里兰州的二层小楼,清晨遛狗,午后修剪草坪,傍晚读英文报纸。 邻居看他总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好奇问是不是想家乡菜。 他指着食谱说:“想吃茴香馅饺子了。” 1980年,台湾作家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把功德林写成“人间地狱”。 记者蜂拥而至,想听“书生杀手”的证言。 “段某人胡说八道。” 周养浩面对镜头只说一句,“共产党给我重生,我不能忘恩。”说完转身就走。 此后他养成个习惯,每年清明给杨虎城墓园寄白菊。 花店老板起初不肯接单,他就自己跑去邮局汇款,附言写“请代购鲜花,费用我付”。 后来老板知道了他的身份,悄悄在花束里多加两支康乃馨。 老板问:“周先生,您这是何苦?” 他望着窗外的梧桐树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欠杨将军一条命,得还。” 1990年夏天,周养浩在庭院除草时突发心梗。 救护车赶到时,他手里还攥着半截水管。 葬礼很简单,除了家人只来了沈醉的女儿。 她放下束菊花轻声说:“我爸让我谢谢您当年没砸死他。” 周养浩的骨灰盒最终没能运回大陆,女儿把它埋在马里兰州的墓园,旁边种了棵白杨树。 2010年,周养浩的外孙女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 最后一页写着:“我等了一辈子,等老蒋,等台湾,等一个‘回家’的机会。可到最后才明白,真正的家,从来不是某个地方,而是心里的那点念想。”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谍谍不休︱云南解放:大特务周养浩被俘,王蒲臣侥幸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