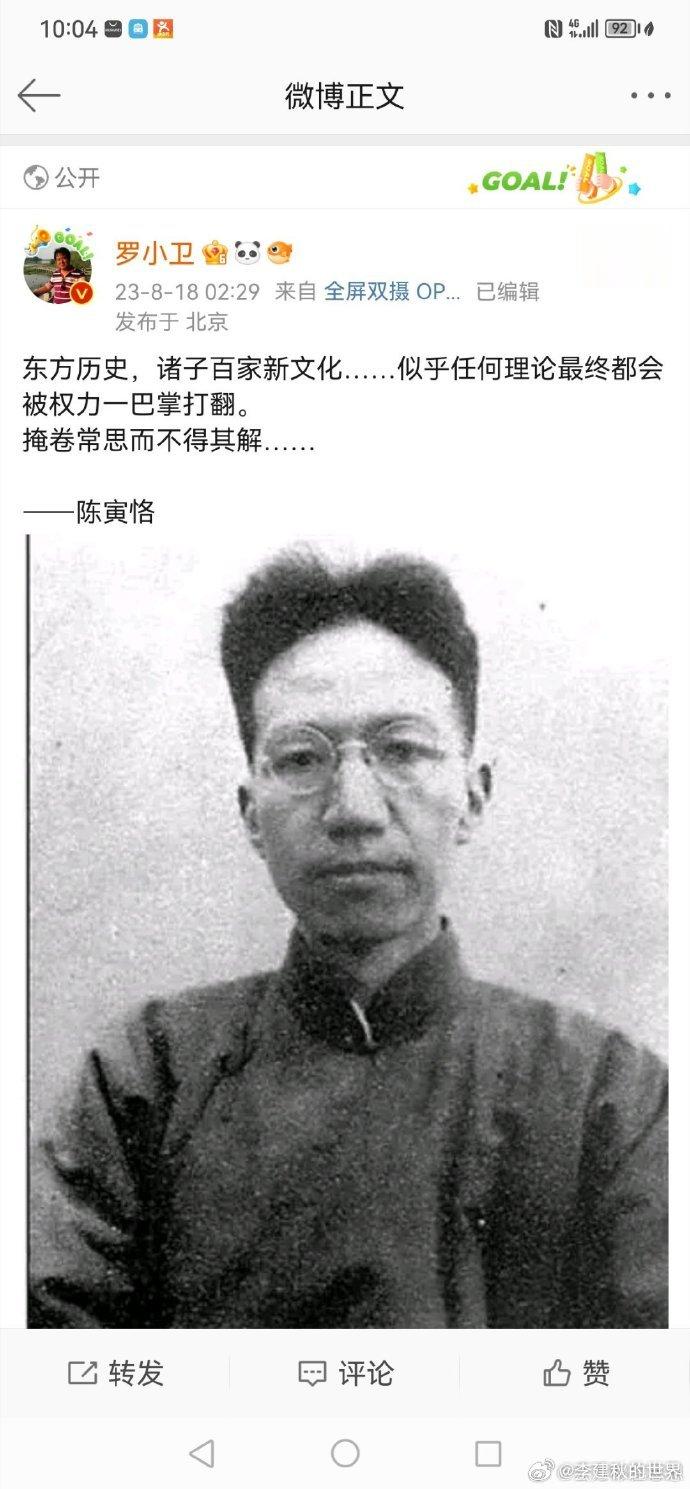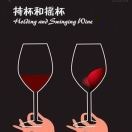我们就拿陈寅格来说。
《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7月21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普遍是这样,知识分子想做事,似乎就是坐在空调室内吹空调,对着外面指指画画,一旦受挫就呼天喊地:
“似乎任何理论最终都会被权力一巴掌打翻”
长征的历史意义就是说,当要实践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不是坐在空调房里面一天到晚瞎逼逼,而是爬雪山过草地,用行动去实践。
陈寅格稍微受了一点压力,就“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怪谁?
怪“任何理论最终都会被权力一巴掌打翻”?
那你活该被打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