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时代的西伯利亚流放,常被人与中国的宁古塔流放相提并论,甚至被认为是沙皇对反贼的“仁慈”。但事实远比这复杂。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并非人人畏惧,其残酷程度也并非一成不变。
西伯利亚的开发,源于沙俄的扩张野心。从哥萨克雇佣兵征服西伯利亚的低成本,到后来廉价甩卖阿拉斯加,都可见沙俄对这片土地的轻视。但广袤的无人区又不得不开发,于是,“流放”成了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选择。
最早的流放,更像是一种震慑。1591年,乌格利奇大教堂的铜钟因叛乱事件被流放,象征着沙皇对谋反的零容忍。此后,流放逐渐替代死刑,成为沙俄处理“反贼”的主要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流放西伯利亚的确让一些人免于一死,但这“恩德”却在大规模的滥用中变了味。
1760年的“流放法”,赋予了地方权力机构无需审判即可流放犯人的权力。这一制度的漏洞,使得大量的底层农奴成为牺牲品。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漫漫长路上,死于饥寒、疾病和劳累。即便侥幸抵达,等待他们的也是无尽的苦役,被当作牲畜般压榨,直至生命终结。
同样的流放,对贵族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参与者被流放西伯利亚。但他们乘坐马车前往,到达后直接进入当地政府任职,享有津贴和自由。他们不是去受苦,而是换个地方继续享受特权,甚至有些人还因此提升了社会地位。
就连著名的革命家列宁,在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三年里,也得到了优待。他母亲的求情信,让他被安置在温暖的南部地区,每月还有8卢布的津贴,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他甚至在那里结婚成家,过得相当滋润。
这种巨大的反差,凸显了沙俄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的执行,取决于身份的高低贵贱。在西伯利亚,真正的残酷,并非来自严寒的气候,而是来自不公的制度。对于农奴而言,流放是人间地狱。而对于贵族,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升迁。
沙俄到苏联的数百年间,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持续存在,改变了数百万人的命运,西伯利亚的开发史也充满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如今,西伯利亚的居民大多是当年被流放农奴的后代,而那些曾被流放的贵族早已重返权力中心,继续书写他们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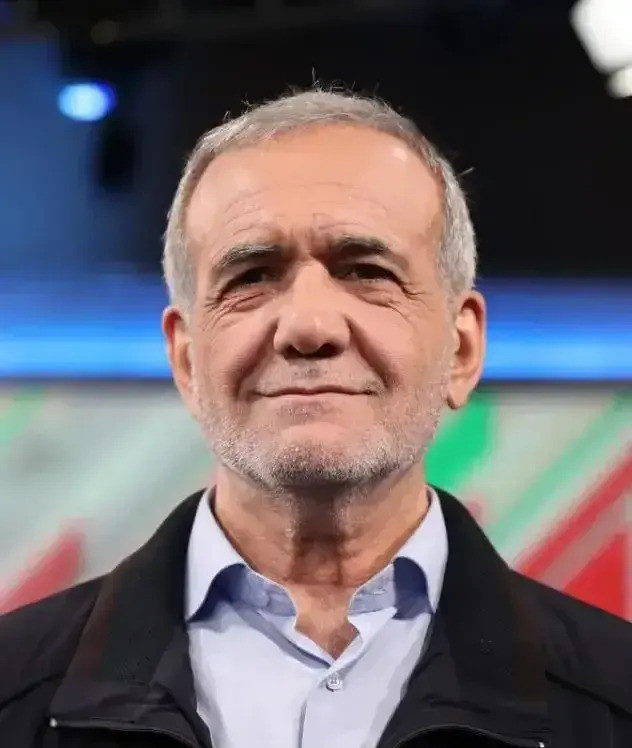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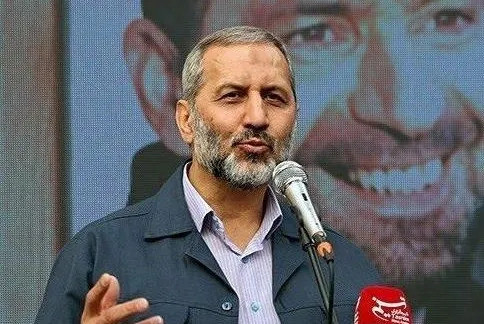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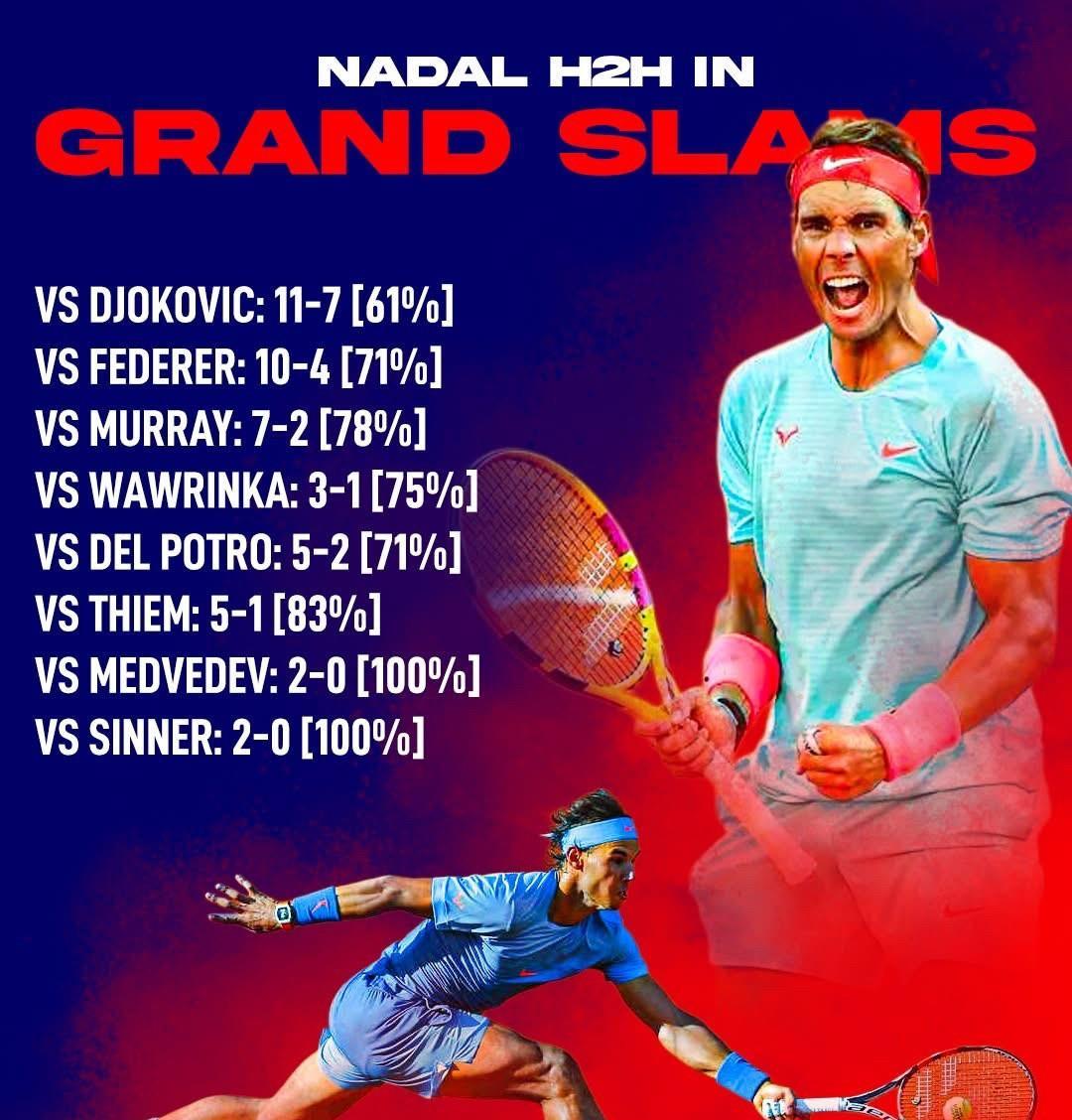

AKD卢
阶级的固化,是一个国家走向衰落的开始!
49xxx77
太平天国没有打到西伯利亚可惜了。
用户18xxx22
流放宁古塔的士绅因为有文化知识在当地同样有一定的地位,很多都被当地八旗优待成私家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