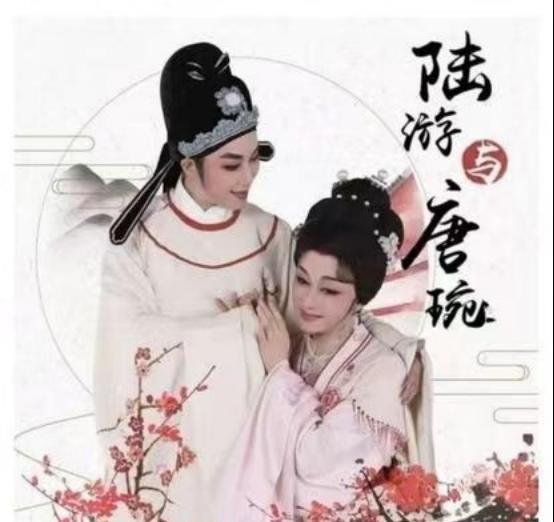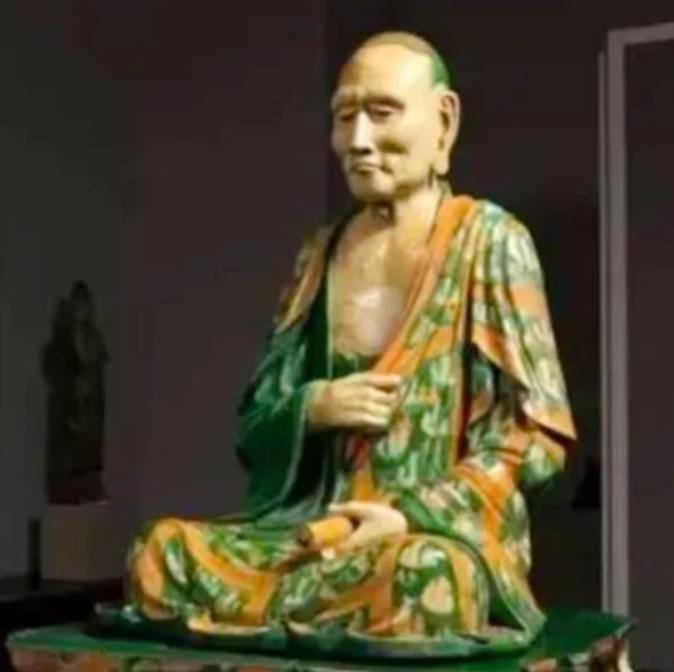张勋晚年闲居在天津的松寿里,独留花白辫子不放,有人劝其要识时务,他手捏辫梢,学着杨小楼的京剧念白说道:“吾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脑袋在,辫子不掉!真吾大清股肱之臣。” 出殡那天,辫子还在头上。路边的老百姓哭,有人笑。有人跪拜,有人吐口水。 张勋的辫子,死也没剪,棺材盖上压着的是“大清忠武”的封谥,地下埋着的是一个不肯转身的旧世界。 早些年就说过:“脑袋在,辫子不掉。”话说得冲,手也硬,剪辫运动搞得天翻地覆,他硬是一动不动。 有人劝:“顺潮流吧,您都退了。”张勋一哼:“回天无力,尚可独善其身。” 像是认命了,其实是倔强。 不是不懂时代变了,是不认这个时代。 说他死心眼,有道理,连演戏都讲忠君。他喜欢杨小楼的念白,茶余饭后就学:“大清江山不能亡,臣子岂可苟且偷生!” 声调一拔,眼圈发红。那不是演戏,是宣誓。 死忠两个字,张勋往死里忠,可辫子不能当饭吃。辛亥之后,当大清忠臣的工资早断了。 张勋没吭声,转身搞实业,别人退位,他退隐;别人混政坛,他做商阀。 一口气投了70多家企业,矿、银行、纱厂、电影、报纸全都有。 天津英租界、德租界、北京城、南昌小洋楼,他的房子比段祺瑞的警卫都多。 自己不炫,手下人给他立功榜一样地讲:“总资产五六千万银元,换成现在,那就是几百亿。” 光是吃,都能吓人,请了扬州名厨,改良菜式,把老家的腌笋鱼头,跟北方燕窝鱼翅搞在一起,独创一道“荷叶稀饭”,早上喝完,全身通泰。 听起来素,其实贵,得用最嫩的荷叶,包五年陈米熬四小时,一锅几十块银元,不是吃饭,是吃钱。 宅子讲究,松寿里大院里头有假山、有凉亭、有戏台,奴仆百来号人,站成两排都能当仪仗队。 每年过年、生日、中秋、端午,少不了唱戏。 戏码不一般,唱戏的人也不一般。 梅兰芳、杨小楼、孙菊仙一请就是一排,来一次堂会能挣几千银元,孙菊仙拿了六百大洋,感动得哭了。 张勋拍拍他肩膀:“这年头忠义无价,艺也如此。” 外面叫他“军阀”,他其实活得像个世外高人,自己号“松寿老人”,天天在院子里写字,练的是颜体,临的是《麻姑仙坛记》,一笔一划,写得比枪法还狠。 读书讲究,《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常放在手边。 嘴里念“忠义”,心里装的还是帝制。 朋友也不一般,什么陈宝琛、陈师曾这类“遗老”,隔三差五来聚一聚,聊旧朝、讲君臣、说格物致知,酒杯一摆,仿佛大清还在。 可他又不是完全脱离世事,表面说“仕途已灰”,段祺瑞、张作霖来请他出山,他摇头;私底下呢? 北洋财政部给他企业撑腰,他收得稳稳当当。商场如战场,他知道怎么保命。 不当官,但能做大老板,再说葬礼那天。 1923年病逝,消息一出,满京城都传疯了,溥仪赐谥“忠武”,孙中山也托人送了副挽联——写了四个字,“愚忠可悯”。 忠武,是给脸,愚忠,是讽刺。 一路送葬,两个月路祭,江西老乡穿麻戴孝;可北京政界,酒桌上议论不断:“一个辫子军阀,死也不懂变通。” 溥仪私下说他粗,徐世昌评论更直:“卤莽灭裂,愚不可及。” 活着争议大,死了争议更大。 有人敬他——忠于所信,死不回头,有人骂他——复辟失败还不收手,留个辫子自我感动。 可不能否认,他是个硬骨头,没剪辫,不是因为不敢剪,而是信那个朝代比命还重要。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想改,是不想骗我自己。” 这个人,活成了符号。 新旧交替的大戏里,他扮演了最后一个,站着不肯谢幕的旧人。 参考资料: 胡健中.《张勋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