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爱玲死后将270万全部留给朋友。而此时她远在国内的弟弟,穷困潦倒。张爱玲为何不把财产留给她弟? 这桩看似冷酷无情的遗产分配案,从来就不是一笔简单的经济账,而是一场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情感清算。 张爱玲自己早就说过:“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她和弟弟张子静,便是最早看穿这一切的孩子。 他们的童年,浸泡在鸦片的烟雾和无休止的争吵里。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空有才情却无担当,将家业一点点败在烟榻上。 母亲黄逸梵是位五四浪潮中的新女性,给了张爱玲艺术的启蒙和远方的向往,却也亲手教会了她现实的第一课,爱是需要计算成本的。 她可以为了女儿的教育和丈夫大闹,像拐卖人口一般把张爱玲送进学校。但当同样流着自己血的儿子张子静,带着一双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站在面前请求收留时,她却冷静地推开了他。 那句家里剩的米只够两人吃,与其说是经济的窘迫,不如说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宣言。在这位母亲的世界里,资源必须投给更有价值的一方。 姐姐聪慧、有前途,值得投资。弟弟体弱、怯懦,则成了被放弃的成本。 这一幕门内的张爱玲哭了,门外的张子静也哭了。但姐姐的眼泪里,恐怕除了同情,更多的是一种被现实烙下的警醒:原来亲情和爱,都是有条件的,是可以被量化、被选择的。 这种金钱与情感的纠缠,成了她一生写作和生活的底色,她后来在小说里反复描摹的那些为了钱而扭曲变形的人性,其最初的蓝本,或许就来自她的亲生父母。 在这个家里,姐弟俩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岔路。姐姐倔强反叛,因顶撞继母被父亲毒打囚禁,她选择逃离,奔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而弟弟选择了顺从,甚至在姐姐与继母爆发冲突时保持沉默。他像一只自轻的小动物,学会在夹缝中将自己变得渺小,以此躲避伤害。 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几乎是残忍地将弟弟的形象投射在主角聂传庆身上,一个阴郁、懦弱、被家庭压垮的精神残废。 这既是她对弟弟不争气的失望,也是她对自己所逃离的那个世界的深刻恐惧。她害怕的,正是那种会把人慢慢磨损、吞噬掉的,黏腻而无望的家庭关系。 所以,当她远走高飞,在美国建立起自己孤绝的王国后,她便用最决绝的方式,斩断了与那个过去的最后一丝牵连。 弟弟张子静在他的一生中,几次试探性地向姐姐伸出手。办杂志约稿,被以不出名的刊物会败坏我的名声为由拒绝。晚年想娶妻,写信求助,收到的回信是没有能力帮你的忙。 这看似不近人情,却是张爱玲自我保护机制的必然反应。在她看来,弟弟和他所代表的一切,正是她拼尽全力才摆脱的麻烦琐事。她不能,也不愿再被拖回那片泥沼。 与这份血缘的疏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与宋淇、邝文美夫妇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情谊。这份情谊始于她1952年困顿于香港之时的雪中送炭。 宋淇夫妇为她租房、介绍工作,帮她联系出版,让她得以在美国安心写作,获得稳定的版税收入。 他们懂得她文字的矜贵,也尊重她个性的孤僻。这份基于才华的欣赏和灵魂的懂得,超越了血缘所带来的天然羁绊。 晚年的张爱玲沉浸在对过往的反复书写中,从《小团圆》到《雷峰塔》,她不再是那个卖弄张腔、精明世故的才女,而更像一个执拗的老人,试图用一种近乎天真的笨拙,去还原、去清算自己一生的爱与憎。 在这个过程中,她最需要的是一个能理解她文学意图的遗产执行人,宋淇夫妇是最佳人选。 她留给他们的与其说是270万的财产,不如说是她一生最珍视的文学声名和那些未竟的手稿。她需要有人为她守护这份最后的体面与真实。 而弟弟张子静,他温厚、善良,甚至在晚年还为姐姐辩解:“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但他终究是她笔下的人物,是她所书的一部分,却无法成为她文章的守护者。 信息来源:《张子静笔下的姐姐:我的姐姐张爱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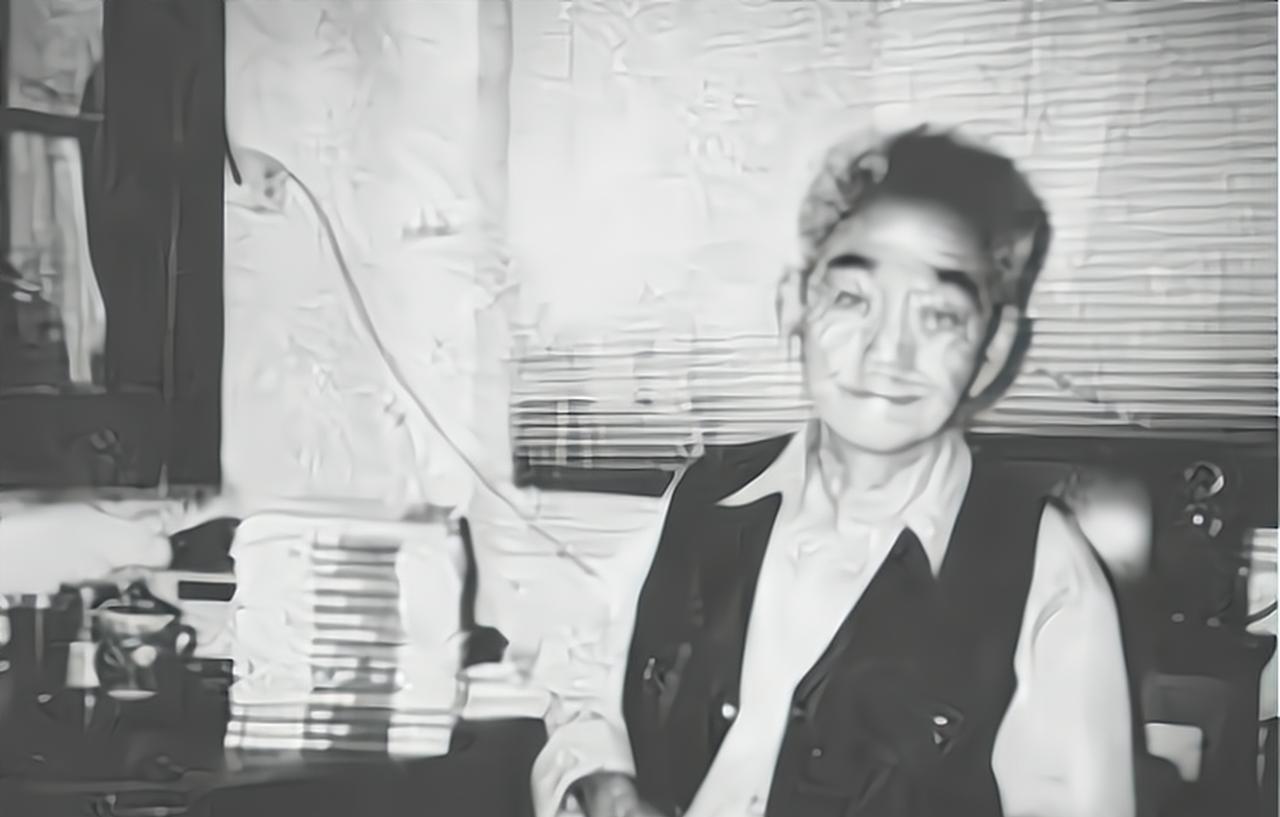

用户65xxx00
女汉奸。
用户65xxx00
女汗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