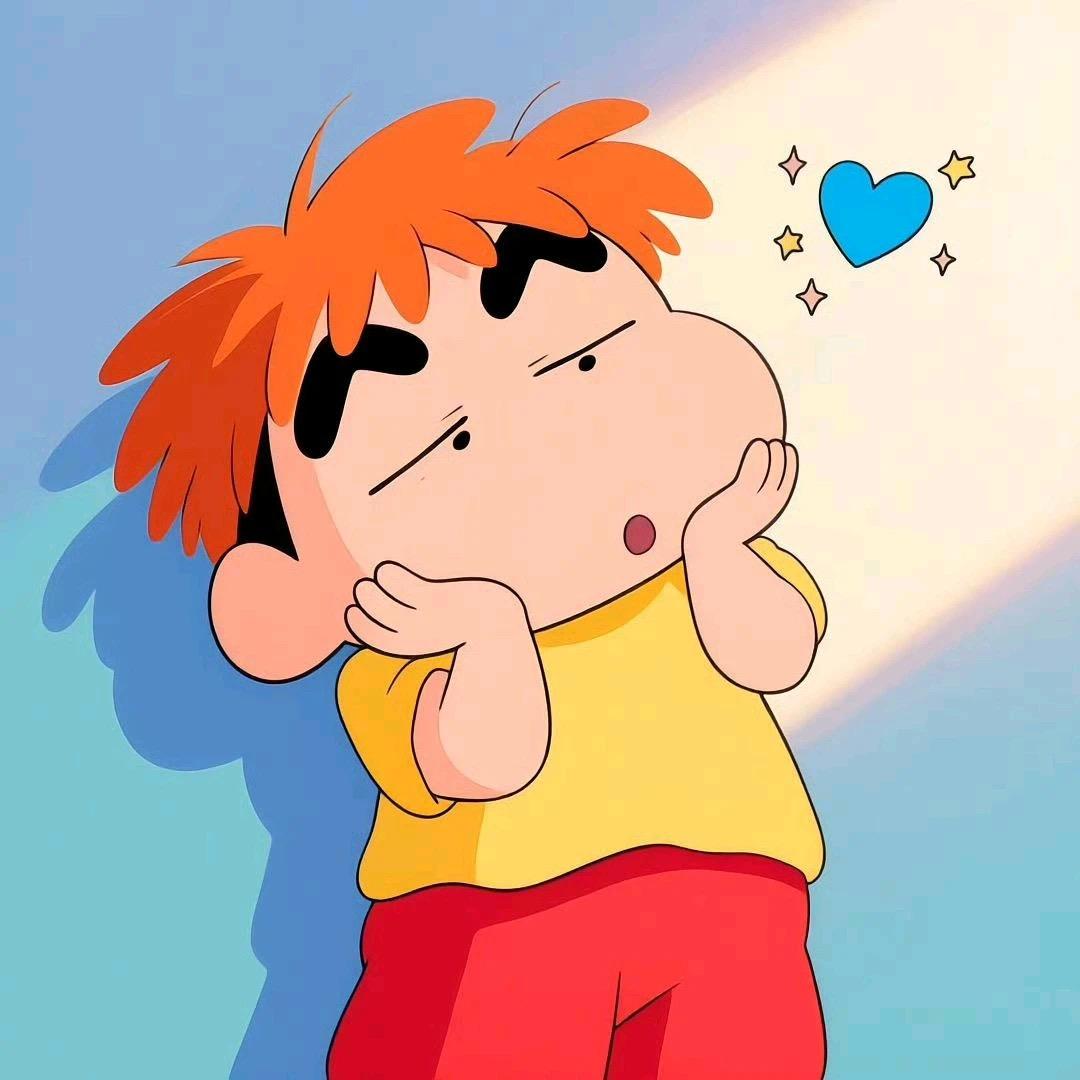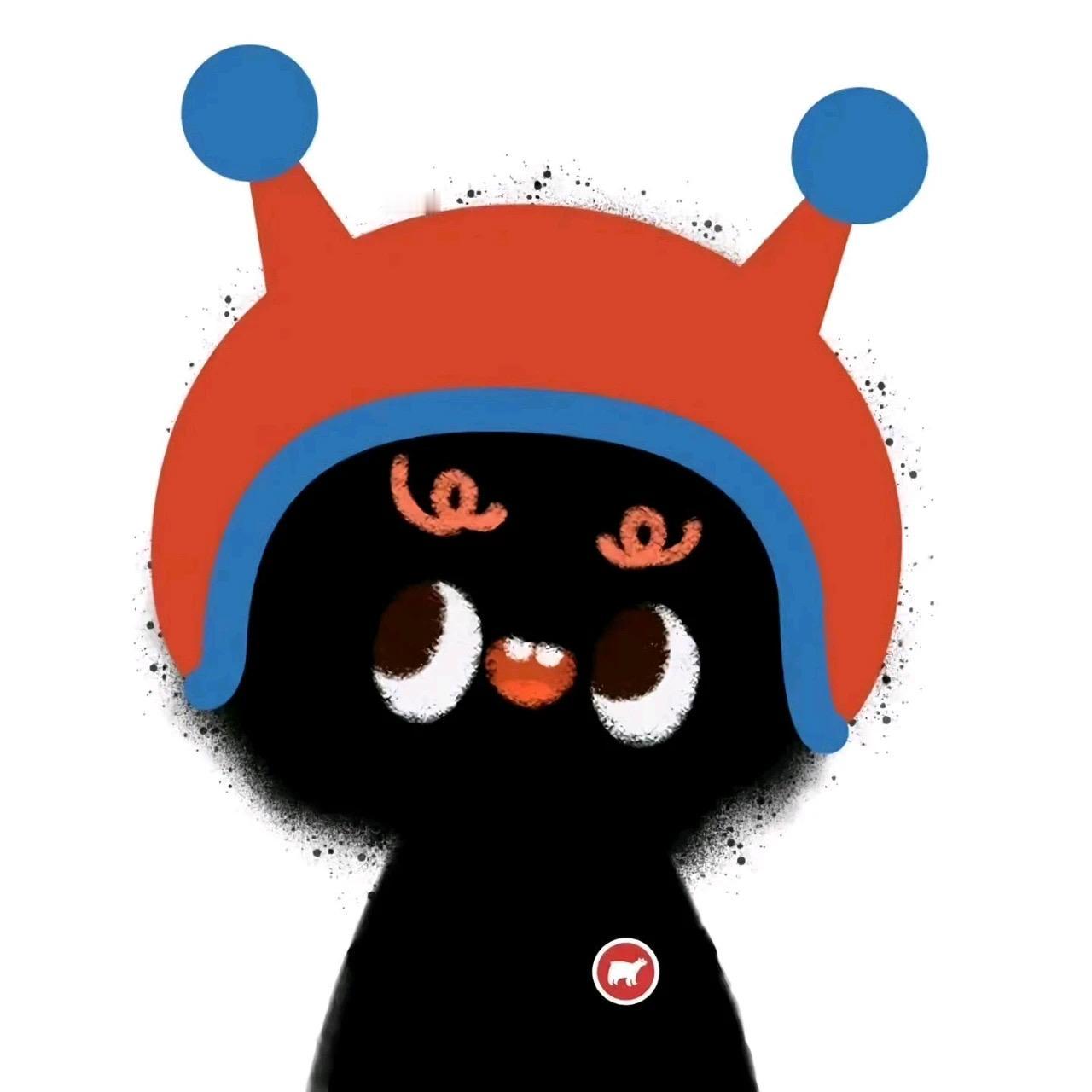腐朽的桃源 所谓“纯天然”的桃源,其内里却蠕动着看不见的蛆虫。泥土里渗出的并非芬芳,而是千年沉积的荒芜与辛酸。当城里人舌尖赞美着“无污染”的菜蔬时,他们无从知晓,祖父辈的肠腹早已被这些“洁净”之物中暗藏的粗粝与匮乏蛀蚀出空洞。 泥土的深处,沉埋着无数夭折的童骸。那些夭亡的魂灵,如无声的根须,在黑暗里吮吸着大地的养分,也吸食着生者的气数。他们的骨殖,被泥土缓慢地消化,最终化为田野里一茬茬沉默的庄稼。这土地并非滋养者,而是一张巨大而缓慢的嘴,咀嚼着所有生于斯、葬于斯的人。 苍蝇是这片土地古老而虔诚的信徒。它们并非无端滋生,而是从这土地的脏腑深处、从茅厕的恶臭与猪圈的污秽里,被一种原始腐朽的力量召唤而来。它们透明的翅膀切割着浑浊的空气,在婴儿啼哭的唇边、在老人溃烂的脚踝上、在每一碗粗粝饭食的上空,跳着永无止境的死亡之舞。它们细碎的嗡鸣,是这片“纯天然”土地上永恒的低语经文。 那被诗人吟咏的“袅袅炊烟”,升腾于无数代农妇龟裂的手掌之上。她们弯腰于土灶前,火焰舔舐着她们空洞的眼窝,烟雾钻进她们积劳的肺腑。炊烟里没有诗意,只有柴草燃烧的呛咳,混合着锅中永远稀薄寡淡的菜羹气味。这烟柱,是村庄向灰白天穹伸出的枯瘦求救手指,日复一日,终被漠然的风扯碎。 祖父曾陷于同一片泥沼。烂泥没至膝盖,冰冷如亡者的拥抱。他挣扎,泥浆发出吮吸活物的贪婪声响。父亲亦曾在此处陷落,咒骂声被同样粘稠的泥泞吞没。如今,轮到孩子。他小小的身体在烂泥中徒劳扭动,泥点飞溅上稚嫩惊恐的脸庞。时间在此处并非流逝,而是一口巨大的泥潭,世代相传的陷落是它唯一的刻度。每一次下沉,都是对宿命笨拙而绝望的摹写。 村中那处露天厕所,是大地敞开的、永不愈合的溃疡。它并非简单的污秽之所,而是一个巨大而原始的陶罐,年深日久地发酵着全村人排泄的浊物。秽气蒸腾,凝结成肉眼可见的绿雾,沉重地悬浮在低矮的茅檐下。这绿雾是活的,它缓慢地爬行,钻进每一道墙缝,渗入每一件晾晒的粗布衣衫,最终沉淀在人们的肺腑深处,成为身体里一块无法咳出的、带着腥臊的淤积。 当那些鲜亮的小汽车碾过新铺的水泥路驶入村庄,它们带来的不仅是“新农村”的标签。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无形的、更为彻底的覆盖。崭新的水泥路如同一条冰冷的白色裹尸布,强硬地覆盖在曾经泥泞不堪的村道上。它封存了旧日挣扎的痕迹,也封存了泥土深处的呼吸与呜咽。苍蝇似乎少了,被某种刺鼻的药剂气味驱赶、压制。然而那气味本身,像另一种无形的苍蝇,更加执着地钻进鼻孔,附着在喉咙深处,宣告着一种新的、化学的统治。 老妇立于新修的、贴着冰冷瓷砖的屋前。水泥地坪坚硬光滑,反射着陌生刺眼的天光。她浑浊的目光投向远处平整得如同塑料假景的田野,那里,大型收割机正轰鸣着吞噬庄稼。孙子小小的身影在田埂上奔跑,突然脚下一滑,再次摔进田垄边仅存的一小洼烂泥里。他惊恐的哭喊刺破新村的寂静。 老妇的心骤然沉了下去,如同当年陷入泥沼的祖父。她终于看清了:这光鲜的新村,不过是覆盖在旧日泥潭上的一层薄薄水泥。时间并未真正流动,它只是凝固了。那些古老的、粘稠的、令人窒息的泥泞,依然在水泥板下、在田垄边缘、在人心看不见的角落,暗暗涌动,耐心等待着下一个失足者。 所谓桃源,不过是时光凝固的泥沼。水泥路覆盖其上,苍蝇暂时噤声,可泥土深处那原始的饥馑与辛酸从未消散。它们只是潜入更深的黑暗,如同蛰伏的根须,耐心等待下一场春雨——抑或,等待水泥板下悄然渗出的、带着铁锈气味的湿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