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在哈尔滨上学,我读两年,我姐读了四年。我三舅在哈尔滨挺有钱的,一次都没去
孟嘉佑阿
2025-07-18 14:21:11
我和我姐在哈尔滨上学,我读两年,我姐读了四年。我三舅在哈尔滨挺有钱的,一次都没去看过我们。倒是有次放假回学校我妈妈让我给三舅带她自己下的大酱,说我三舅就爱吃这口。
那年我刚上大一,抱着装大酱的玻璃罐在哈尔滨站转车,罐口用塑料布仔细扎着,生怕撒出来。按妈妈给的地址找到三舅家,是个带电梯的高档小区,保安登记时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打量。开门的是三舅母,烫着卷发,穿着精致的家居服,看到我手里的玻璃罐愣了一下,才不冷不热地让我进门。
三舅不在家,三舅母给我倒了杯水,全程没问我和姐姐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只是盯着电视里的购物频道。我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说:“舅妈,这是我妈自己下的大酱,说三舅爱吃。”她瞥了一眼罐子:“放厨房吧,他最近减肥,不爱吃这些了。”我看着厨房台面上琳琅满目的进口调料,突然觉得手里的玻璃罐格外寒酸。
没坐十分钟,三舅母就说:“你三舅今晚有应酬,要不你先回去?学校宿舍关门早吧?”我赶紧站起来告辞,她甚至没起身送我到门口。走出小区时,哈尔滨的风刮在脸上生疼,手里的空书包轻飘飘的,心里却堵得慌——原来在有钱的亲戚眼里,我们这样的穷学生根本不值得费心。
姐姐比我早两年到哈尔滨,早就习惯了三舅的冷淡。她在大学城兼职发传单,冬天冻得手通红,却从不说要去找三舅帮忙。有次我跟她抱怨:“三舅太过分了,咱们在这儿上学,他都不来看一眼。”姐姐叹口气:“人家忙着做生意,哪有空管咱们。妈让带大酱是尽心意,咱们别指望别的。”
但妈妈总念叨:“你三舅小时候最疼你,现在条件好了,肯定能帮衬你们。”她每年都要亲手做些咸菜、酱菜,让我们给三舅送去,说:“都是家里的味道,你三舅肯定想家。”有次我忍不住说:“三舅母根本不当回事,上次的酱估计都扔了。”妈妈红着眼圈说:“好歹是亲戚,礼数得到。”
真正让我改观的是大二那年冬天。姐姐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我手里的生活费根本不够住院费。给家里打电话,妈妈急得在电话那头哭,说这就去借钱。正六神无主时,医院催着缴费,我咬着牙给三舅打了电话,心里根本没抱希望。
没想到三舅半小时就赶到了医院,还带来了医生朋友。他没问太多,直接去缴费处交了押金,又安排护工照顾姐姐,转身对我说:“别告诉你妈,省得她担心。你姐恢复期间需要营养,这钱你拿着买吃的。”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塞给我,手指上还沾着机油,大概是从工地赶来的。
我愣在原地,三舅拍了拍我的肩膀:“在外面上学不容易,有事别硬扛,跟三舅说。”这才发现他穿的羽绒服袖口都磨破了,不像三舅母说的那样“天天应酬”。后来护工说,三舅来的时候满头大汗,说是从郊区工地开车赶过来的,闯了两个红灯。
姐姐出院那天,三舅又来了,还带来个保温桶,里面是他让三舅母熬的小米粥。“刚手术别吃油腻的,喝点粥养养胃。”他看着姐姐苍白的脸,皱着眉说:“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兼职别太拼命,钱不够跟我说。”姐姐红着眼圈说:“三舅,谢谢你。”他摆摆手:“谢啥,我是你舅。”
那天三舅才说,他不是不想来看我们,是怕三舅母不高兴,“她那人好面子,觉得你们家条件一般,总说怕被拖累。”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妈每年给我带大酱,我都舍不得吃,知道是她的心意。你们在哈尔滨上学,我早托朋友照看着,知道你们俩丫头懂事,不想麻烦人。”
他还给我们留了个电话:“这是我工地上的号码,24小时开机,以后有事直接打这个,别打家里电话。”临走时他又说:“别跟你妈说这些,省得她胡思乱想。亲戚之间,帮忙是应该的。”看着他开车离开的背影,我突然明白,有些人的好,从不在嘴上,而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
后来我才知道,三舅生意做得并不顺利,前两年投资失败赔了不少钱,正靠着工地的活儿慢慢回本。给姐姐交的手术费,是他刚结的工程款。妈妈寄去的大酱,他每次都分给工地的老乡,说:“这是我姐做的,有家的味道。”
毕业那年,三舅来学校帮我们搬行李,特意请我们吃了顿饭。席间他喝了点酒,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当年家里穷,是你妈辍学供我读书,我才有今天。你们俩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别忘本。”他眼圈红红的,不像平时那个沉默寡言的舅舅。
现在我和姐姐都在哈尔滨工作了,常去看三舅。三舅母对我们也热络了,说:“你三舅总念叨你们,说俩外甥女有出息。”妈妈寄来的大酱,她会主动拌上黄瓜端上桌,说:“还是家里的味道香。”
每次想起那些在哈尔滨的日子,心里都暖暖的。原来亲情从不是表面的热络,而是藏在心底的惦记;不是锦上添花的客套,而是雪中送炭的真诚。三舅或许不善表达,却用最实在的行动告诉我们:亲戚之间的情分,从不会被距离和贫富隔断,只要心里装着对方,关键时刻总能挺身而出。
0
阅读: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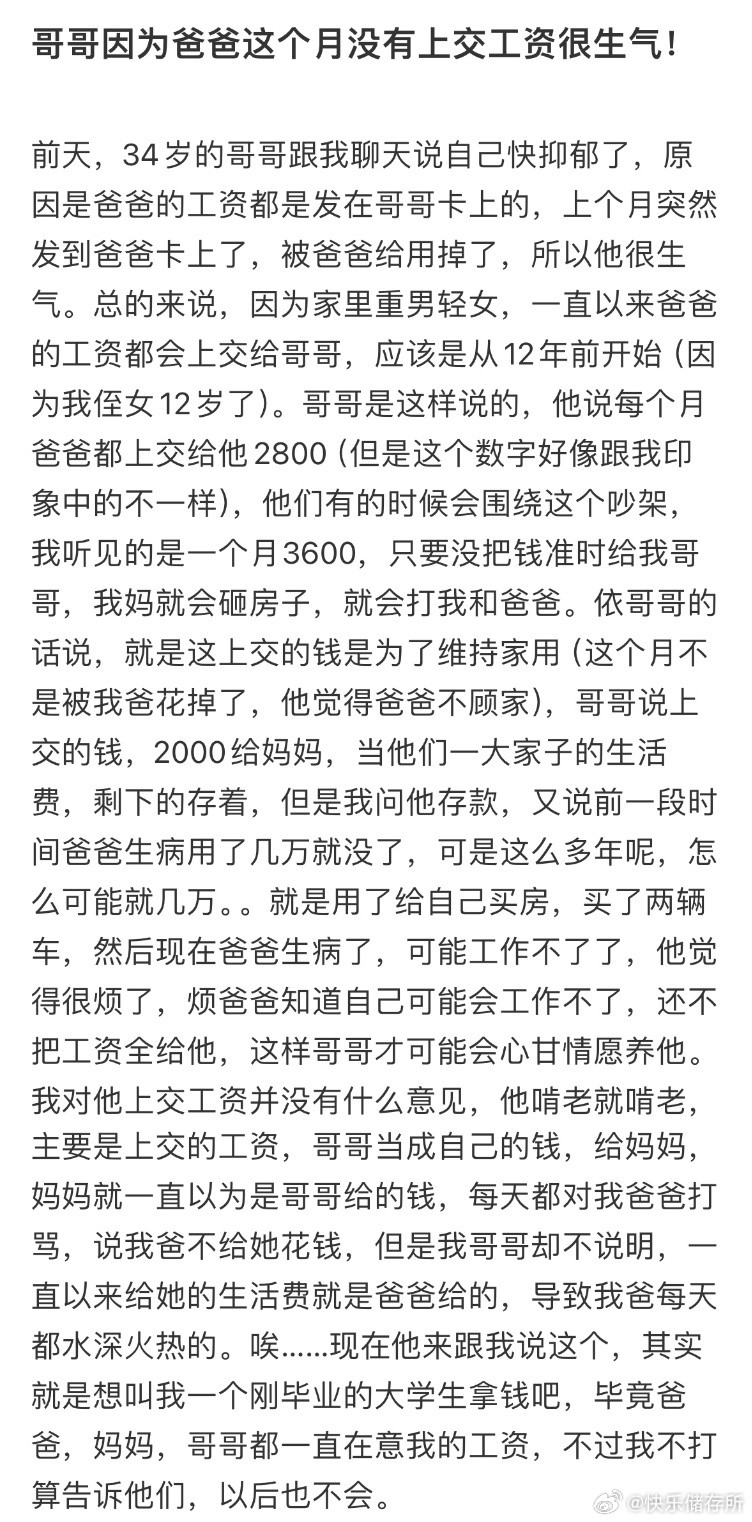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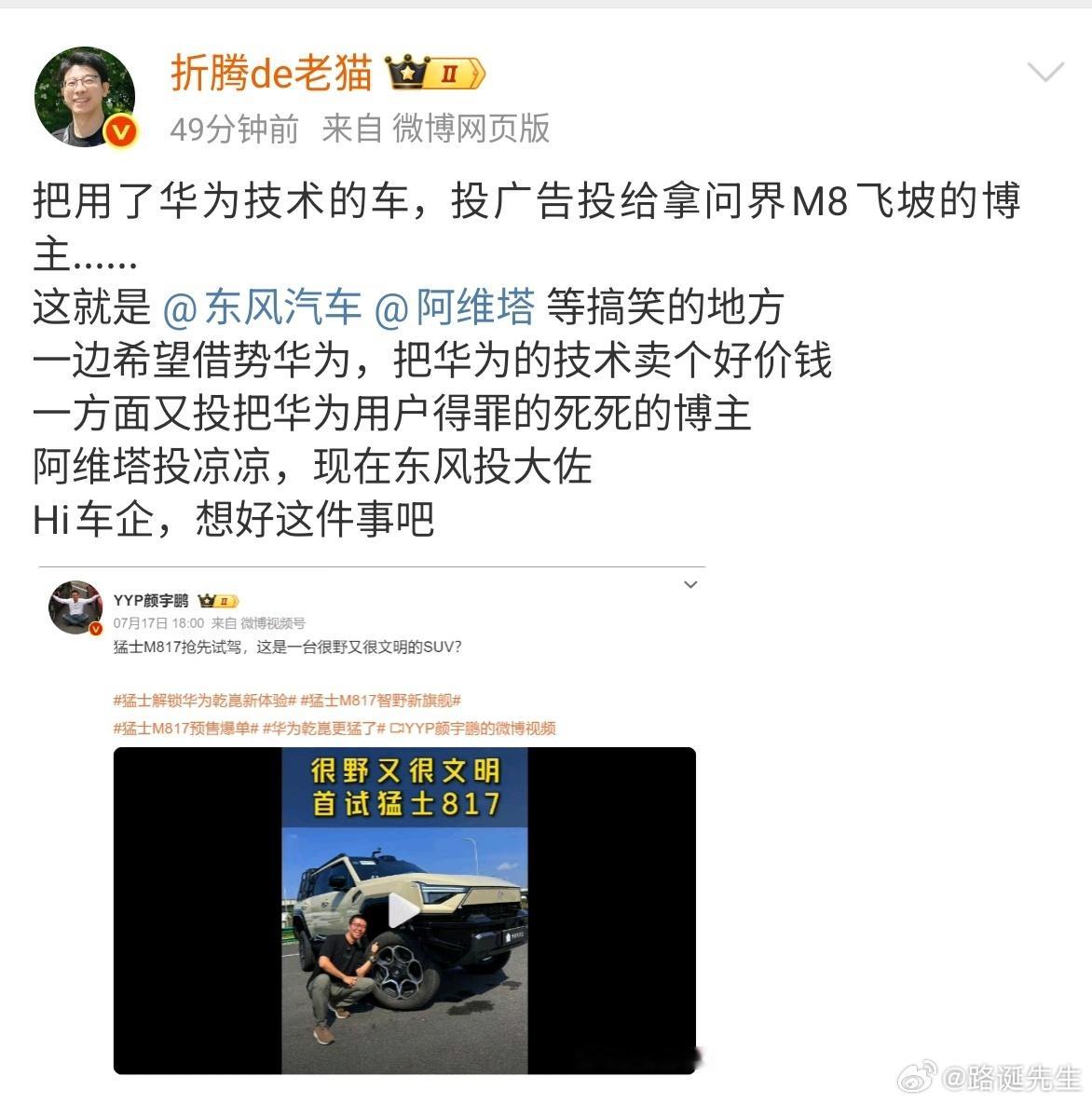



![人家说这是邮政,不是民政!哥,你羞什么呢[大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爱晒太阳的人,](http://image.uczzd.cn/830797343641660862.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