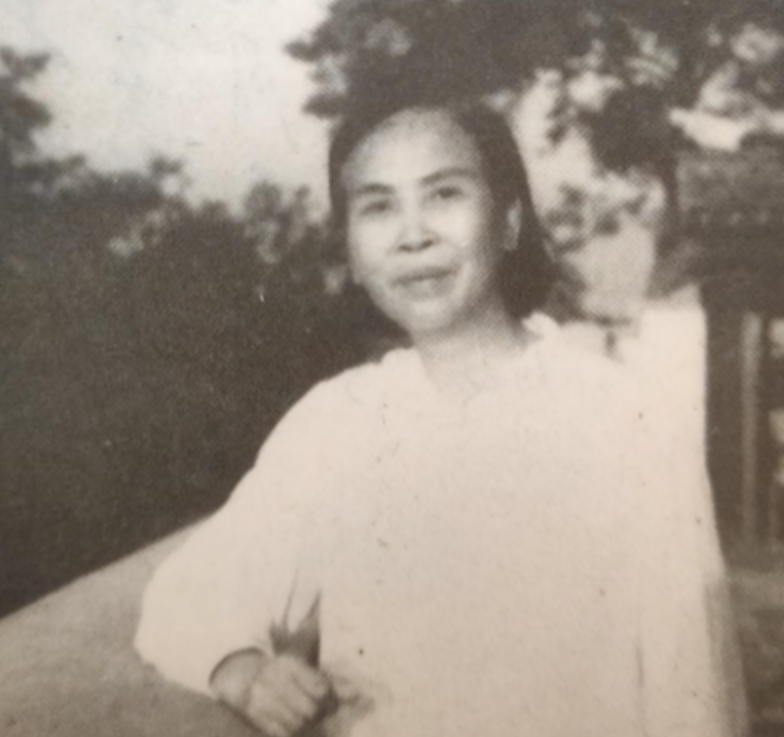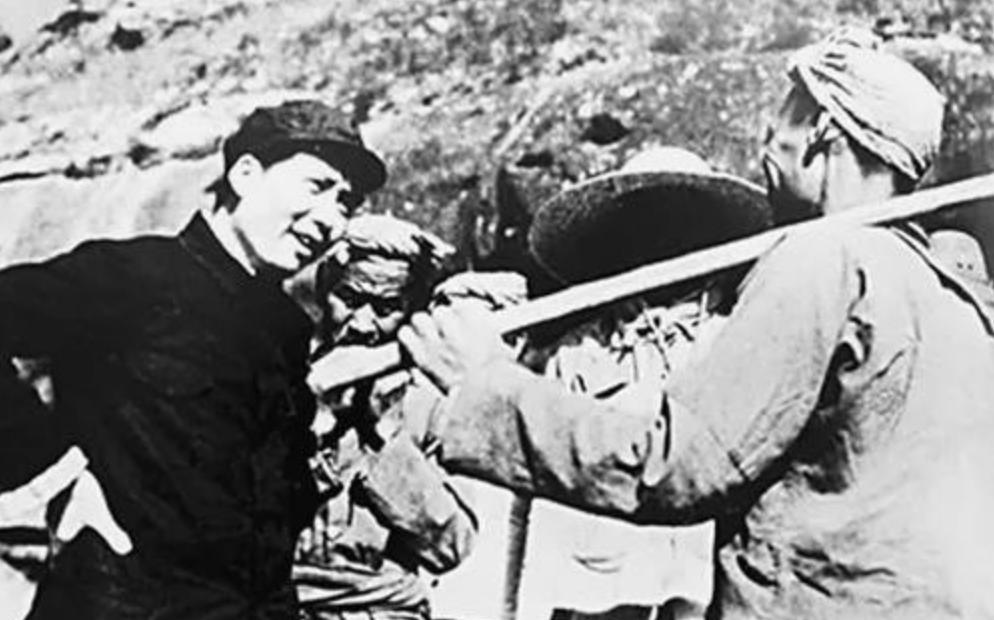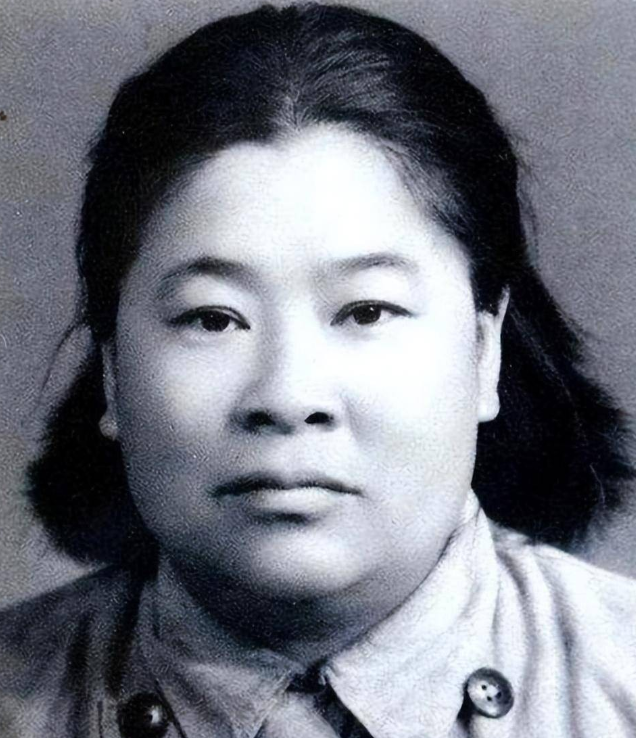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1952年的一个夏天,在湖北大冶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年过半百的铁匠正在炉边忙活,他叫朱其升,是镇上出了名的“老实人”,打了一辈子铁,手艺好,但话不多,炉火映红了他布满老茧的手,屋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空气中弥漫着铁屑和煤烟的味道。 这天傍晚,邮差敲响了他家的门,手里是一封盖着红色印章的挂号信,信封厚实,背面印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字样,朱其升接过信,愣了好一会儿,手指微微颤抖,像是握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他不识字,只得请邻居帮忙读信,那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落款是毛泽东。 那一刻,朱其升的眼眶湿润了,许久未曾提起的记忆,像炉火中的碎铁屑,一下子被烧得通红,他没有立刻说话,只默默收起信,转身回到屋里,把信封放进木箱最底层,对于他来说,这封信不是荣耀,而是一段被时间封存的往事,悄悄地在心里扎了根。 四十多年前,朱其升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出生在湖南石门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里穷,饭都吃不饱,为了贴补家用,他跟着父亲学打铁,早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那时的中国正值风雨飘摇,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年轻人都想着投军变命运,他离开老家,辗转来到长沙,希望能靠一身力气找到出路。 长沙当时是个乱中有序的地方,街头车水马龙,兵招四起,朱其升报名参军,被编入湖南新军,分到了一个基层号兵棚,训练苦,日子紧,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新兵营里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个叫毛润之的青年,身材瘦高,说话不多,但总是眉头紧锁,眼神坚定,他们住一个营棚,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渐渐相熟。 朱其升是个实在人,见谁缺啥都会搭把手,毛润之没有棉衣,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让给他穿,打饭排队,他也总是帮人占个位置,其实他也穷,但他从不计较这些,那些日子,兵营条件差,长沙的冬天冷得刺骨,夜里冻得睡不着觉,他们靠着一团火取暖,靠着一口气熬过去。 新军很快解散了,许多人各奔前程,毛润之回了乡,后来听说他继续读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朱其升则回到老家,重新拿起铁锤,那些年的日子,像炉火里的铁条,一锤一锤地砸过来,他在湖北大冶落了脚,娶了妻,养了孩子,生活虽清苦,但也算安稳。 战乱不断,日子时好时坏,有时候几天都打不到一单活,家里揭不开锅;有时候却能连着几天加夜班,干到手肿背酸,他从不叫苦,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命,可他心里始终记得那个在长沙共过寒冬的青年,那双眼睛,那份沉静,仿佛早就预见了未来的风雨。 新中国成立那年,乡里家家户户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朱其升第一次看到那张画时,整个人都怔住了,他盯着画像看了很久,越看越觉得熟悉,那眉眼,那神情,和他记忆中的毛润之几乎一模一样,他没有立刻说出口,甚至连家人也没提,这个秘密,他埋在心底,像炉灰下的一点余烬。 直到1952年,他终于鼓起勇气,托镇上的私塾先生帮他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可能冒昧了,但他实在无法忘记那段日子,他不求什么,只想知道,那时候的朋友,如今是否安好,信寄出去了,他没抱太大希望,可谁知,几个月后,他真的收到了回信。 毛泽东在信中称他为“其升兄”,还清楚地提到当年在新军兵营里的情景,信里没有大话,只有一份温情,他还寄来了一笔钱,让朱其升改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做点实事,朱其升读完信后,沉默了很久,他不是感动得流泪的人,但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炉边,把那封信反复读了三遍。 他没有用那笔钱为自己置办新房,也没有去做什么铺张的事,他把钱拿来,在镇上开了一家油布伞厂,他知道南方雨水多,老百姓家家户户都需要伞,他用自己做铁的手艺,亲自打造伞骨,带着几个年轻人学艺,慢慢把伞厂办了起来,他给伞厂起名叫“和平”,说这是个能遮风挡雨的名字。 伞厂开起来后,日子渐渐好过了,原本靠打铁糊口的他,成了带动乡里就业的“朱老板”,可他从不张扬,那封信,他用红布包好,锁在柜子里,不让外人看,也不拿它来说嘴,他常说:“人活着,总得干点实在事,” 1956年,朱其升受邀前往北京参加轻工业会议,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也是最后一次,中南海的会客厅里,他见到了毛泽东,两人时隔四十多年再次相见,没有铺张的场面,也没有仪式感的拥抱,他们只是坐下来喝了顿茶,说了些旧事,毛泽东鼓励他继续发展实业,说国家需要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