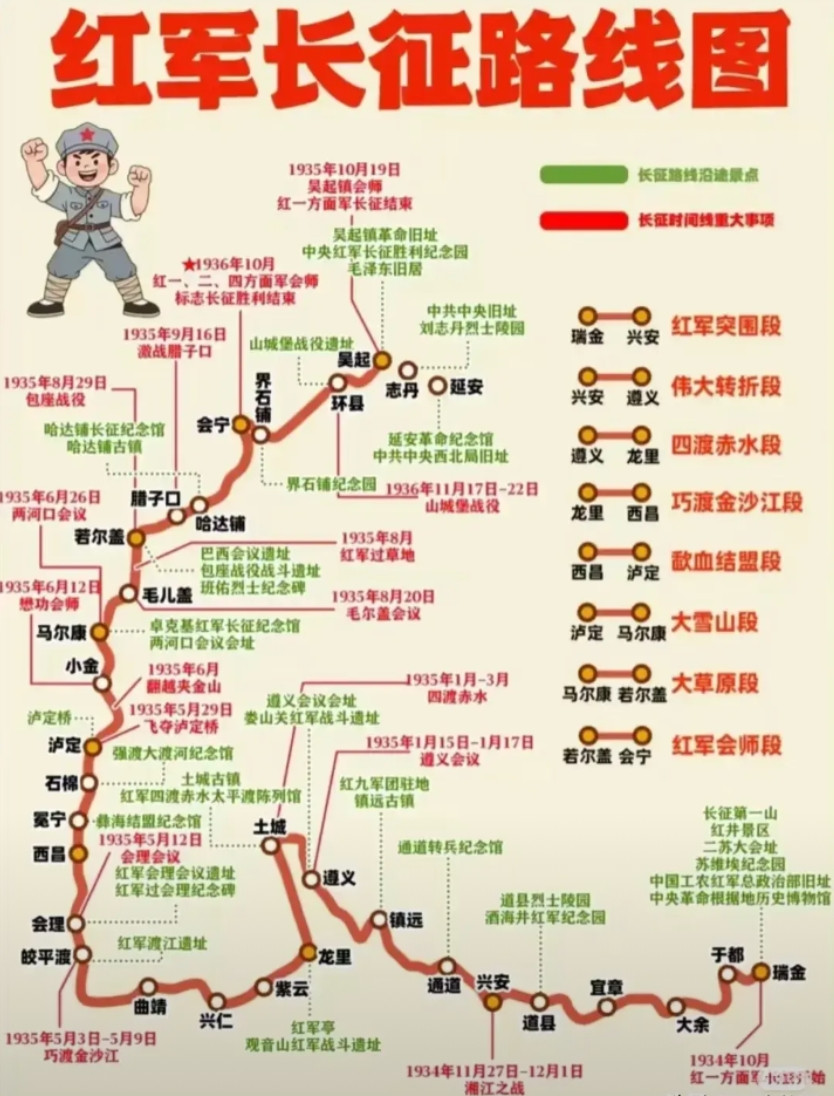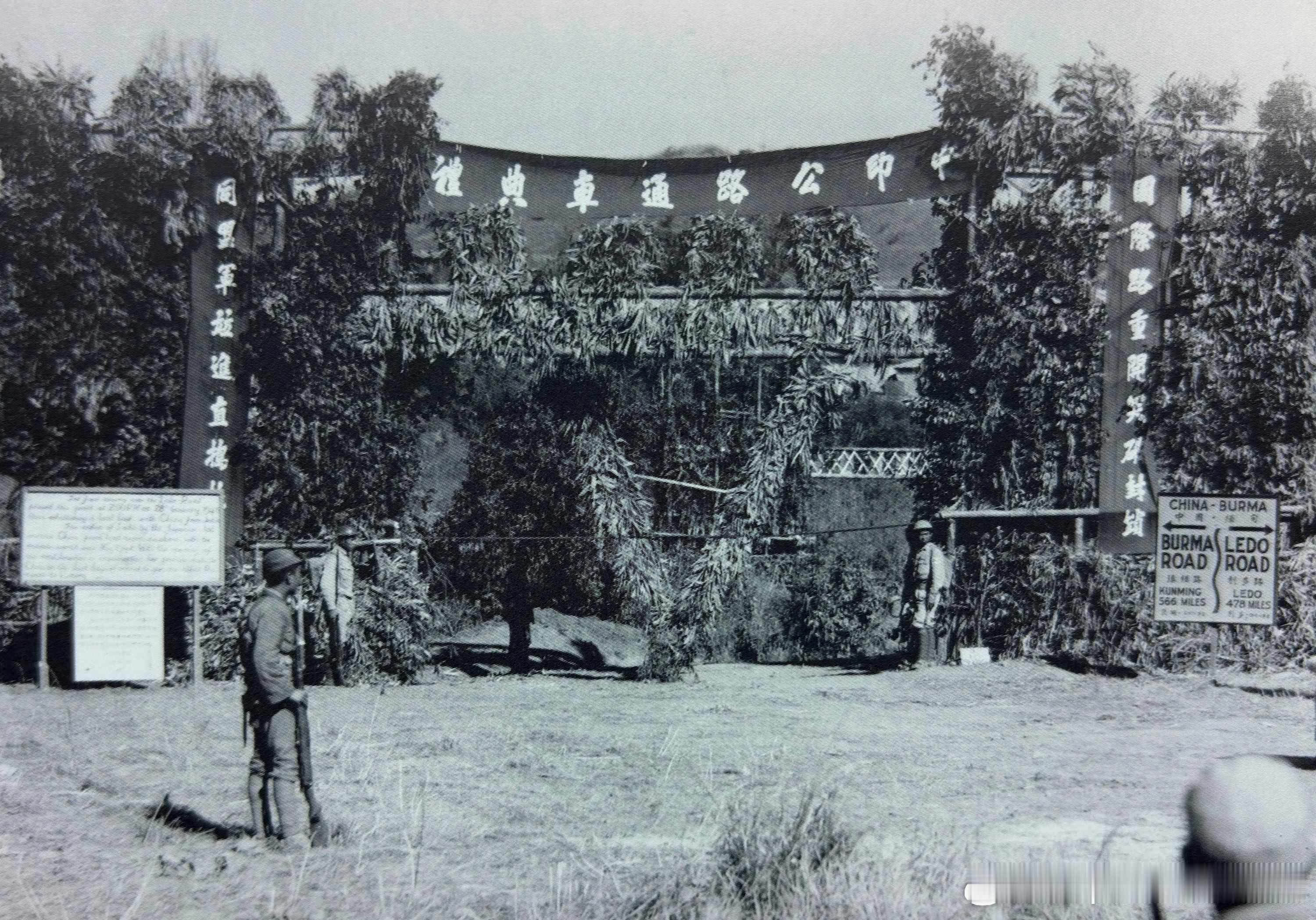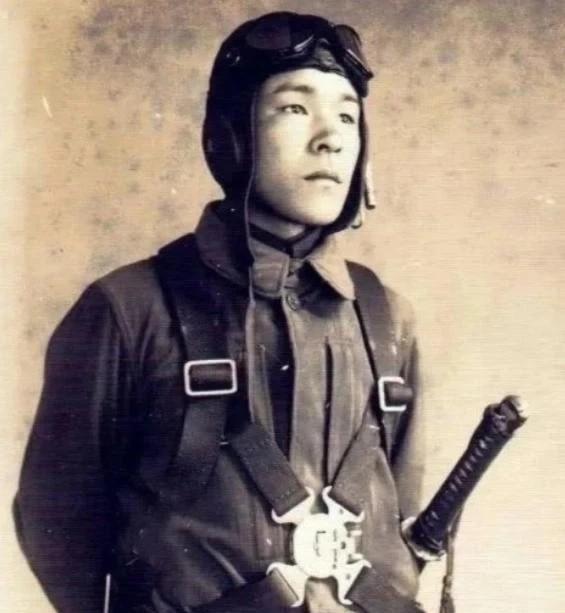1945年,在山上休息的迫击炮手陈宝柳,忽然发现40多个日军,正在路过不远处的榕树下,他悄悄架起迫击炮,打算给他们来一发狠的!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5年春,赣南山林依旧湿重,藤蔓缠绕在斑驳树干上,云雾从山顶一线线滑下,像是将时间拖慢了许多,陈宝柳背着他的迫击炮,一步步踩在半干不湿的松叶上,缓慢地在山坡一隅坐下。 几天的行军让人精疲力尽,连衣领都泛着硬硬的盐白,他从包袱里掏出抹布,擦拭着炮管上的水汽,神情专注。 他没想到,就在这片山坡下的洼地边,一棵老榕树的浓荫之下,竟聚着四十多个日军,他们卸下了武器,脱掉鞋袜,有人用罐头盖盛着水喝,几个斜倚在树根上的人正抽着烟。 他望着这一切,没有惊慌也没有犹豫,只是静静地停住了动作,陈宝柳出身温州乡村,自幼种田放牛,臂力过人,眼力更胜,被抓进部队时,他甚至连枪响都未曾亲耳听过。 新兵的日子被催促着前进,他学装枪、学辨声、学着在死人堆里找出活路,他曾抬着受伤的老兵穿越山谷,也曾在夜战中踩过自己兄弟的遗体,满脚温热。 进入炮兵连,是因一次临时换人,正副炮手都伤了,长官急召替补,他接过坐标簿的时候,满手都是血。 他当时什么都不懂,只是靠着自己对地势的敏感和力气将炮架扶稳,凭着一次观察留下的印象拉了扳索,炮弹在两山之间炸开,像撕裂了天,他没被表扬,也没人教他技巧,从此每一场战斗,他都靠自己记下炮角和坐标。 眼前的情形不能拖,陈宝柳轻轻放下炮身,从布包中取出三发炮弹,检查引信与底火,他从地面起伏判断距离,从风穿林叶的方向修正角度,他的身影几乎与地面平齐,像林中的一块石头。 他不急,像是在等一个沉稳的节拍,等风静,等云散,等敌人的姿势更松懈一些,他开始装填,毫无声响,第一发炮弹呼啸而出,炸点落在榕树右侧,震起一大片尘土。 惨叫声在山谷回荡,接连的两发弹随后跟进,分别击中堆放物资的位置与外围的低洼通道,爆炸将地面掀出焦黑的窟窿,碎片刮落树叶,烟雾久久不散。 他没有多看一眼战果,也没有停留清点,收起炮架,背起包袱,顺着东南方向的小道迅速离开了那片山坡,他始终知道,这种时候留下就是送命,没人会为多杀几个敌人而容忍迟滞。 当他回到队伍所在的密林时,已是黄昏,阳光斜斜落在他肩头,队伍依旧静默,他的身上多了烟火与泥土的气味。 这一击的影响远远超出预期,后续的部队绕路搜山时,确认了战果,一小队日军被全歼,所携轻武器与补给也尽数摧毁。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炮击让敌军误以为主力已经接近,开始主动收缩清剿范围,为游击队的转移赢得了两日喘息。 陈宝柳没说什么,奖章没有他的名字,通报也只是笼统提及“火力压制成功”,他继续挪着炮架走山岭,在山风与尘土里度过战争最后的几个月。 抗战胜利的那天,没有喧嚣的庆祝,他接过遣散证与一小包干粮,独自往南走了三天三夜,才回到温州近郊的村口。 村子与记忆里大不一样,土墙斑驳,门槛低矮,炊烟也稀薄,他站在家门口,妻子从屋后走出来,认了他好几分钟才流泪开口,他把背包卸下,背上的炮架痕早已磨成了一道深红的印子。 他没再提那场炮击,也不说战事,重新握锄头下地时,手掌还会因伤口裂开疼痛,他咬着牙继续干,不让家里人察觉。 村里孩子们偶尔问他当兵的事,他只是摆手,他不爱说英雄,也从不提爆炸声,他用最熟悉的方式回归生活,修水渠、种田地、养猪养鸡。 直到很多年后,县里追查老兵时,有人翻出当年炮击记录,才找到这个在档案中被称作“精准如刻”的射手,但他早已不在人世,只留下一个破旧的炮镜和一枚用红布包着的黄铜识别牌。 这场战斗没有雕像,也没有纪念碑,只是当人们走过榕树下的那片洼地时,会听见老人们说起,有那么一个农家娃,用三发炮弹给敌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那年山林寂静无声,烟雾升腾,又归于沉寂,可那些从田垄走上战场的人,用最沉稳的脚步,走出了一个国家的生路。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93岁抗战老兵陈宝柳:三发炮炸死40个日本兵——温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