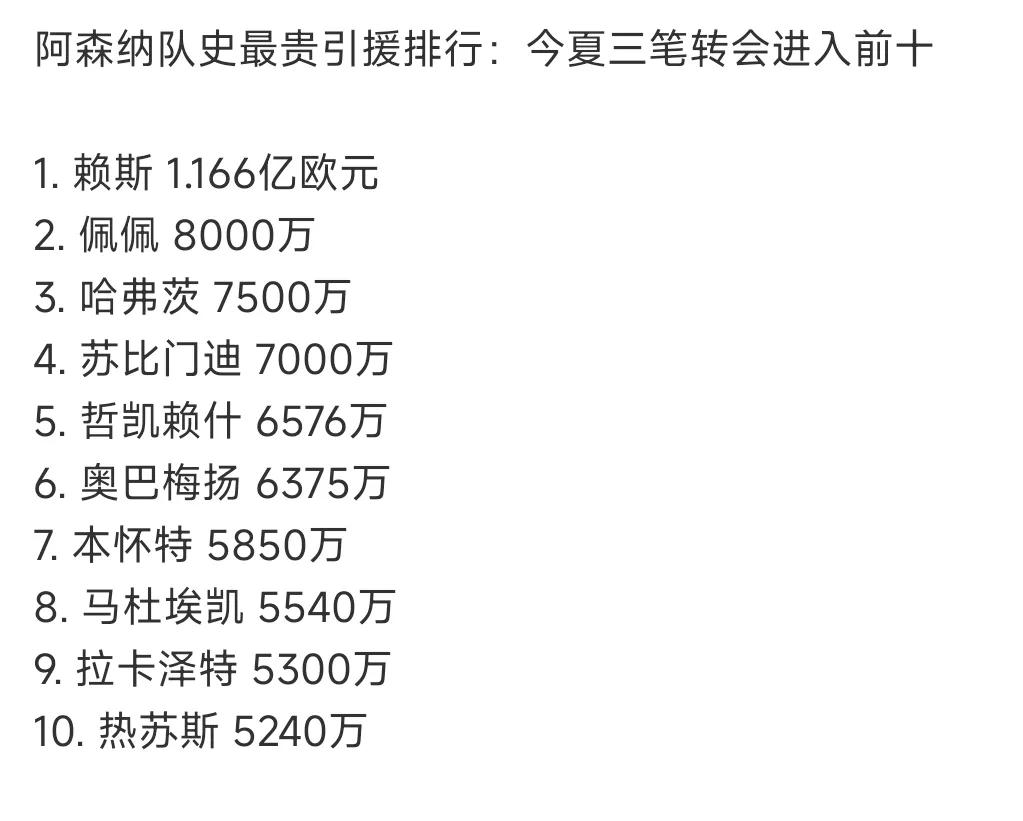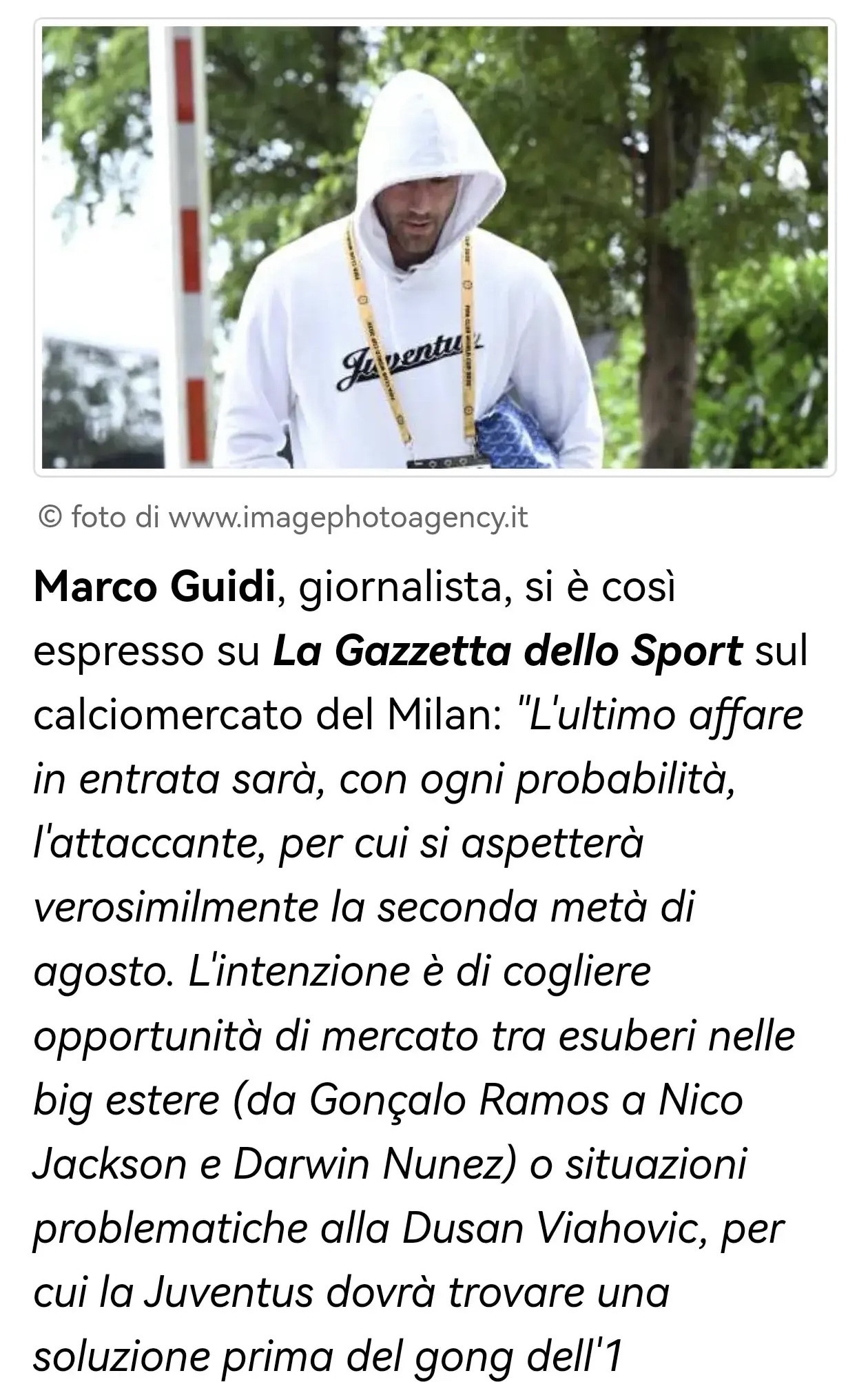新京报:在告别乒乓球比赛多年,30岁的关口,你为什么选择重回赛场?
朱雨玲:我从来没觉得年龄于我是一种障碍,当年离开赛场的不得已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觉得是个“逗号”,或者说没有好好地告别也是一个遗憾。所以当能重回赛场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是既激动又忐忑的,激动的是我又能拿起久违的球拍去到熟悉的赛场中,忐忑的是我是否还有能力去竞技?是否还能坦然地面对失败?身边大多数的朋友都觉得我这样挺折腾,没苦硬吃,可我内心始终有一个坚定的声音:二十多年只专注的这一件事,就算是轻拿轻放,也应该有机会好好地告个别,那才是对生命、对梦想最好的尊重。
新京报:多年后重返赛场,你付出了哪些努力?
朱雨玲:复出的确不易,但我从未回头看过,只顾着一直向前。现在回想这段经历,就是一腔热血被现实教育的真实写照。训练停歇了几年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身体机能降低,恢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需要重新找回身体状态以及技术水平,接受简单粗糙的训练环境和训练状态,还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事务性工作。
这种考验不光是体力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我要面对坐十几个小时飞机,结果(比赛)一轮游的尴尬,可能正是因为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人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激发,我不再是以往在国家队时候的“要我练”,现在是“我要练”。
复出的第一场比赛是澳门冠军赛女单比赛,比赛前一晚,我既激动又忐忑,更有久违赛场的陌生感。虽然最后我止步16强,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像做梦一样,从来没想过能健康地再回到赛场上。
新京报:在本次WTT赛事中,你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被媒体称为“迟来的复仇”,你战胜了5年前两次不敌的对手,这场比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雨玲:在我的世界里从未对对手有过仇恨之心,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如何攻破颗粒打法的比赛。伊藤美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永不服输的精神,我非常欣赏她这一点。而且她作为乒乓球历史上首位混双奥运冠军,又是特殊打法,走到今天,被无数的运动员研究打法,但她永远在想办法创新她的技术,目的就是为了赢。如果我是教练,我一定希望能遇上这样的运动员。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决赛对手陈熠,你认为哪些原因使你取得了胜利?
朱雨玲:陈熠是一名非常有潜力的选手,从去年年底我们俩从低级别比赛赛事一起打到大满贯,她这一路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今年四月的WTT太原常规挑战赛我们曾有过交手,可以说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决赛时她还是表现出了年轻运动员的冲劲,我做好了赛前准备,所以不至于慌乱。我在局中捕捉到机会实现了逆转,在这场比赛中,经验是获胜的关键吧。
新京报:经历疾病治疗,复出后在这次重大比赛中夺冠,你有怎样的感受?站到领奖台那一刻,心情是怎样的?
朱雨玲:拿到奖杯的那一刻,我看了它一眼,想确认着奖杯上写的是什么。看到了champion 我才意识到今天的冠军是我。这不是我获得的分量最重的冠军,却是我当下最有意义的冠军。
新京报:2020年8月,你因为身体免疫系统出现问题退出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入院治疗。在治疗的这段时间你的心态有没有变化?后面是怎么慢慢调整心态的?
朱雨玲:我其实在2019年身体就出现了不适症状,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每天正常的训练也能坚持下来,在奥运周期里多少会有一些(对成绩的)期待。直到2020年症状加重影响到训练时,我才感受到身体不堪重负,去多家医院的检查结果都是4a级的结节(存在恶性可能),建议手术治疗。我很清楚手术治疗意味着什么,我想奥运会是无望了,但是第二年的全运会还是不能放弃,反复思量后我选择了保守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治疗,症状明显减轻,病灶也在缩小,我又重新回到了训练场。“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时候我对这句话有了具象的理解。但是命运偶尔也会开个小小的玩笑,全运会封闭集训期间,大运动量的训练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导致身体出现疼痛症状,夜不能寐,第二天的训练精神也无法集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训练没有价值,这样的坚持也没有意义,于是果断决定放弃比赛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手术治疗。
新京报:你曾说这段治疗经历对你来说很特别、很有收获,可以展开说说吗?
朱雨玲:第一次体验全麻手术的滋味,躺在病床不能动弹,那一刻很无力也无助,也迫使我正视自己的未来,也在这一刻更加明白珍惜生命的意义,在健康面前什么都不重要。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乒乓球带给了我无限的荣光,也带来了诸多的伤痛,离开(赛场)只是人生的注脚之一,与其在淤泥中挣扎不如潇洒转身,去探索另一条成功之路,所以痊愈后我决定去大学深造。
新京报:手术后,你到家族公司任职,去读博,还去天津大学任教,这几段和乒乓球运动员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朱雨玲:手术过后意味着我将告别赛场重新出发,重新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也都是新奇的。读书一直是我内心极其渴望的事情,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学生生涯的缺失是短板,现在有了去大学深造的机会,我非常兴奋。在面试环节导师提问读博的目的时,我坦率回答,不是为了文凭,而是为了寻找答案,我想知道自己迎难而上能上到哪里。这时的我无知者无畏,还给自己的挑战加上了重重的砝码——全英文论文及答辩。等真正上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基础太薄弱了,简单的经济理论在我这里就是晦涩难懂,而运动员勇于挑战、直面困难的本性帮助了我,不懂就问,向老师和同学虚心请教,慢慢地我领会到了学术研究的魅力。之后,天津大学向我抛来了橄榄枝,给我的事业打开了新的大门。从最初的紧张担心到现在的游刃有余,我和学生之间亦师亦友,相互鼓励。
新京报:你在赛后采访时说,不知道比赛还能打多久,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希望梦能做得长一些。参加比赛对你来说是一场梦吗?
朱雨玲:现在参加乒乓球比赛对于我来说是快乐的,美好的,也是我最擅长的,虽然我现在的职业是大学老师。过往的种种经历让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能够身心健康地回到赛场上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我珍视赛场,珍视对手,珍视每一分球。人的一生没有那么多设想,想多了未必就敢做,而我只想做好每一天。
新京报:你说在赛场上,运动员是耀眼的星,走下领奖台,你是一个普通人,要过自己的生活。你对以后生活、比赛的规划是什么?
朱雨玲:喧嚣过后终将归于平淡,走下领奖台,我更希望保持独立清醒的状态从零开始,继续下一场比赛,或者继续探索教学方法、开展论文的研究。目前我的主业还是大学老师,要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其次是运动员,在有限的时间里安排训练和比赛。另外还要在缝隙时间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
拥有多重身份之后,我的世界变得大了,乒乓球在我眼里就小了,所以胜负对我而言没那么重要了。或许正是这样的心态,我在比赛中有了更好的发挥。
新京报:想对你的学生说什么?或者有一些故事想分享的吗?
朱雨玲:从我复出以来,我的学生们一直在鼓励我。有一次比赛前,我担心没有系统训练,会输给名不见经传的选手,我的学生听到说,老师你这么怕输的话那就永远别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你就永远不会输。
这句话激励了我,让我更有勇气直面挑战。无论我身处高山或是低谷,我的家人、朋友、学生、球迷们都能与我同频共振,这是我感到无比幸运和自豪的事情,我想说相遇是缘分,借用苏轼的一句词与大家共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朱雨玲谈因病错过奥运和全运朱雨玲具象化真诚永远是必杀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