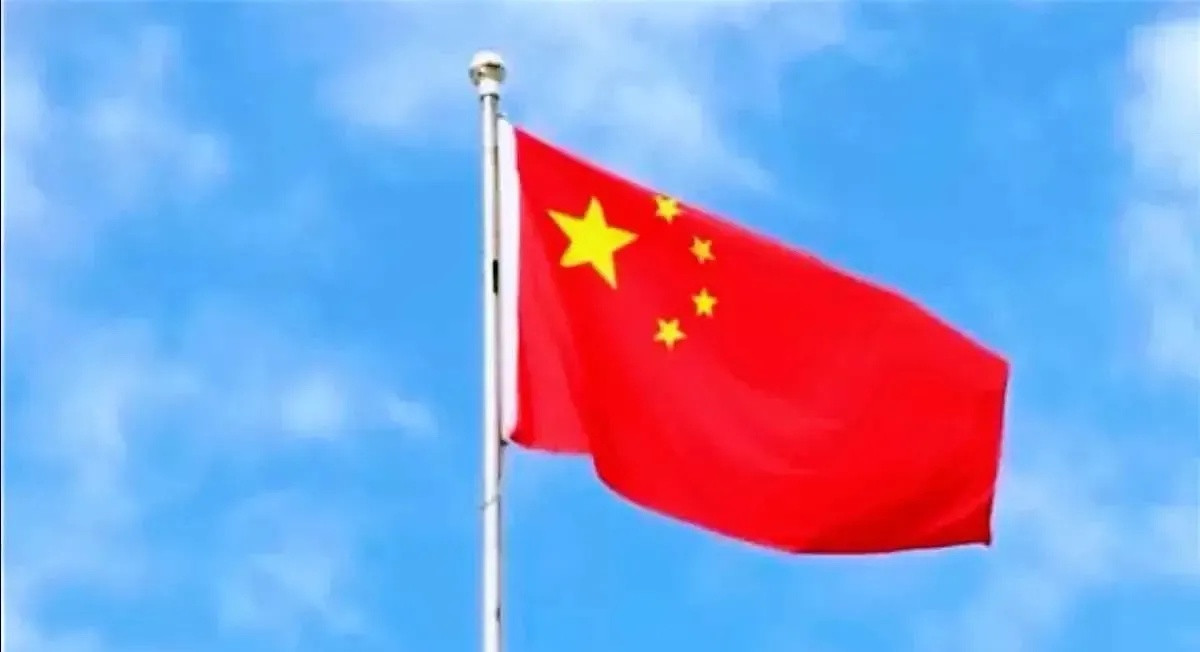1986年,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来墨脱边防的军营视察,却看到军营三百多人全都身着便装,他怒斥:“为何不穿军装!” “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穿军装?!”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将军眉头紧锁,生气的质问带队班长。 一旁的三百多名战士身上穿的,是红的、蓝的、灰的、打着补丁的、甚至褪了色的五颜六色的便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穿军装呢?难道另有隐情么? 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名叫墨脱,藏语意为“隐秘的莲花”,风景绝美,却有这与世隔绝的险境。 它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南麓,被雪山环抱,唯一的“出口”是雅鲁藏布江切割出的峡谷。 这里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所有物资,全靠人背马驮,翻越海拔落差超过4000米、终年积雪的多雄拉山口。 从最近的波密县城到墨脱,直线距离不过120公里,但一趟运输,往返需要整整8天! 这8天,所有运输队的战士们,每人背负着数十公斤的物资,在悬崖峭壁间仅容一人的羊肠小道上挪动。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必经的“蚂蟥区”。 战士们即便在裤腿上涂抹柴油,用塑料布紧紧包裹,也防不住它们无孔不入,钻进衣裤,吸附在皮肤上疯狂吸血。 一位叫王建国的班长,一次运输归来,从身上硬生生拔下了47条吸饱了血的蚂蟥! 腿上留下的血窟窿,足足三个月才勉强愈合。 运输的代价,高昂得令人窒息。 有限的运力,必须优先保障维系生命的粮食、救命的药品和必需的弹药。 军装? 它成了可以被暂时牺牲的“奢侈品”。 整个边防营,三百多名官兵,竟只有87套勉强称得上“完整”的军装! 这些军装只有在执行特殊任务、迎接检查或重要场合时才舍得拿出来穿上。 平日里,官兵们只能穿着五花八门的便装执勤、训练、生活。 更令人心酸的是军装本身的脆弱。 墨脱年降雨量高达2350毫米,是北京的四倍! 军装洗后,挂在屋里三天就能长出一层白毛,晾在外面不到半小时,又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浇透。 反复的潮湿、霉变、晾晒,再结实的布料也经不起折腾。 营长的解释,每一个字都像沉重的铅块,砸在傅全有将军的心上。 他脸上的怒容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震惊、痛心和深深自责的凝重。 他沉默地听着,目光扫过战士们身上打着补丁的便装,最终停留在那些年轻却写满坚毅的眼睛里。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向这支穿着便装、却以钢铁意志守卫着国门的队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下来的三天,傅全有将军执意跟随一支小型运输队,亲身体验墨脱运输线的艰险。 他踩着战士们踩出的泥泞小路,攀爬陡峭的崖壁,穿越令人头皮发麻的蚂蟥区。 他亲眼看到战士们如何在负重几十公斤的情况下,手脚并用地爬行。 更亲眼目睹了警卫员在湿滑路段失足滑向深谷,万幸被一棵崖边小树拦住,才避免坠入雅鲁藏布江激流的惊险一幕! 这趟亲历,让将军彻底明白了那身“便装”背后,是怎样一种难以想象的牺牲与坚守。 回程的飞机上,傅全有将军望着窗外沉默良久。 墨脱官兵的困境,让他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决心。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改变这一切! 回到军区,傅全有将军立刻展开行动。 他亲自协调空军,为墨脱开辟了每月两次的固定空投航线。 然而,墨脱狭窄的山谷、变幻莫测的云雾,让空投充满风险。 十次飞行,往往有三四次因天气恶劣被迫返航。 即使成功进入空域,投下的物资也常因气流影响落入雅鲁藏布江或挂在悬崖峭壁上。 但这已是当时条件下,能争取到的最佳方案。 同时,将军责令后勤部门,专门为墨脱边防研发新型军装! 新军装必须适应墨脱特殊环境,采用速干面料,重量比普通军装轻30%,干燥速度快一倍。 每套军装配备专用防潮密封袋,解决潮湿霉变问题。 1987年春节前夕,第一批500套崭新的、为墨脱量身定制的新军装,终于通过空投,稳稳降落在边防营的操场上! 那一刻,整个营地沸腾了! 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抚摸着那崭新布料,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 1988年,在将军的强力推动下,墨脱历史上第一条能通拖拉机的简易土路开始修建。 虽然简陋,却将物资运输成本降低了60%。 到1990年,墨脱边防官兵终于实现了“每人四套军装”的配置标准。 如今,墨脱早已通了公路,天堑变通途。 但那些曾经穿着便装、在蚂蟥区跋涉、在多雄拉山口搏命的老兵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年代。 主要信源:(新华网——“我为能参与推动青藏铁路的修建感到自豪”——专访原总参谋长傅全有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