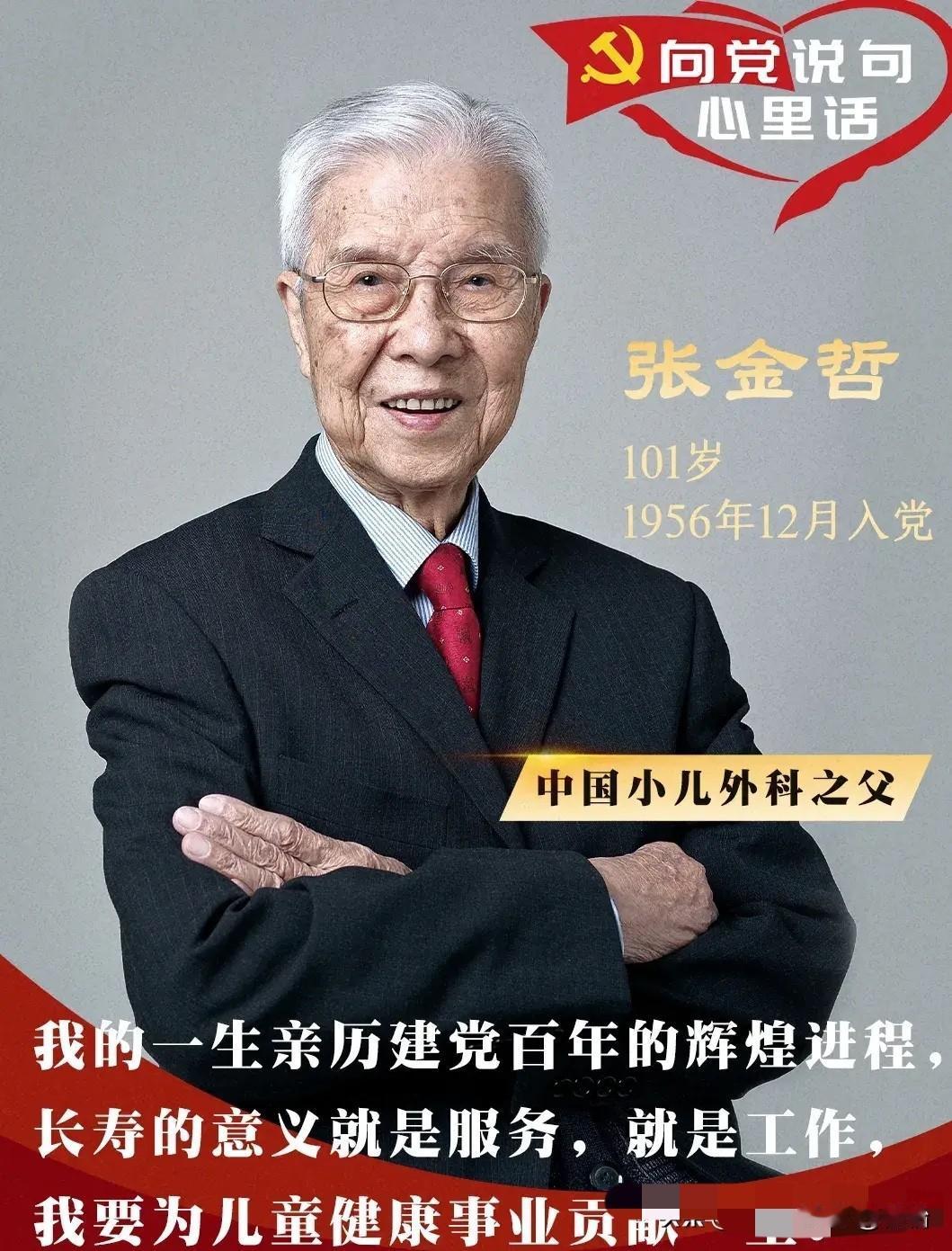1948年8月的一天,儿科医生张金哲痛苦地割开女儿后背溃烂处,黑乎乎的血块流出,他赶紧清理干净,再用力挤出血块再清理,一遍又一遍,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他祈祷奇迹发生..... 张金哲那时候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儿科医生,日子过得紧巴巴,医疗条件也差得要命。 女儿患的是急性骨髓炎,后背肿得像个馒头,皮肤都溃烂发黑了。那会儿青霉素是“稀罕物”,医院仓库里只剩两支,还得留给“重要人物”用。张金哲跑遍了北京城的药房,腿都跑细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 同事劝他“送协和试试”,他红着眼摇头:“协和的床位早满了,等排到号,孩子早没了。” 他是医生,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烧得迷迷糊糊,喊着“爸爸疼”,心像被钳子夹住似的。 没办法,他只能自己动手。家里的饭桌当手术台,用煮沸的白酒消毒手术刀,妻子在旁边举着煤油灯,手都在抖。割开溃烂处的瞬间,恶臭扑鼻而来,黑乎乎的脓血涌出来,混着碎骨碴。张金哲咬着牙清理,手指被划破了也没察觉,只是反复念叨:“别怕,爸爸在。” 女儿疼得尖叫,抓着他的胳膊咬出深深的牙印,他硬是没躲——后来他总说,那牙印比手术刀划的还疼,疼在心里。 其实张金哲早不是普通儿科医生。他从燕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留学英国学过外科,回国后专攻小儿疾病,见过太多孩子因为缺医少药夭折。可轮到自己女儿,他才真正尝到“无力”的滋味。清理完伤口,他用粗布蘸着盐水给女儿包扎,夜里就守在床边,每隔一小时量一次体温,体温表上的刻度,比任何病历都让他揪心。 奇迹还真让他等来了。半个月后,女儿的烧退了,后背的伤口开始收口。那天早上,女儿虚弱地说“想喝粥”,张金哲跑到胡同口的粥铺,买了碗热粥,一勺勺喂她,眼泪掉进粥里,他赶紧擦掉:“快吃,吃完爸爸带你看鸽子。” 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奇迹,是自己一遍遍清理伤口、硬生生把感染压下去的——那些天,他把所有休息时间都用来查资料,从旧医学杂志里翻出“持续引流”的土办法,用竹筒做引流管,每天亲手换药,手指泡在药水里,脱了一层皮。 这事成了张金哲心里的刺,也成了他后来的动力。1950年,他在北大医院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病房,特意把病房弄得像家,墙上画着卡通画,护士站备着糖果。 有次遇到患骨髓炎的穷人家孩子,他掏出自己的工资买抗生素,跟护士说:“我闺女当年没这条件,这些孩子不能再遭罪。” 他还琢磨着改进手术器械,把成人手术刀改小,适合孩子纤细的血管,有人笑他“瞎折腾”,他说:“孩子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得有专门的规矩。”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为女儿亲手清创的医生,后来成了中国小儿外科的奠基人。他首创的“张氏钳”,至今还是小儿疝气手术的常用器械;他编写的《小儿外科学》,培养了几代儿科医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他看着办公室里女儿送的画,画里是个举着手术刀的医生,旁边写着“爸爸是超人”,突然红了眼眶:“我哪是超人,当年连女儿的病都差点治不好。” 他总说,医生的软肋和铠甲,往往是同一个人。为女儿治病的痛,让他懂了家长的心——每个哭闹的孩子背后,都是揪着心的父母;也让他更坚定,要让更多孩子能被好好医治,不用再像他女儿那样,只能靠父亲的手硬扛。 那些在简陋条件下的坚持,那些混合着泪水和脓血的清创,终究化作了后来小儿外科病房里的灯光,亮了七十多年。 现在的孩子很难想象,当年连一支青霉素都稀缺的年代,有位父亲兼医生,用最原始的办法,一边疼得掉泪,一边硬撑着救女儿,还想着“不能让别的孩子再这样”。这份从个人痛苦里生发出的职业担当,或许比任何奖杯都更能说明“医者仁心”的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