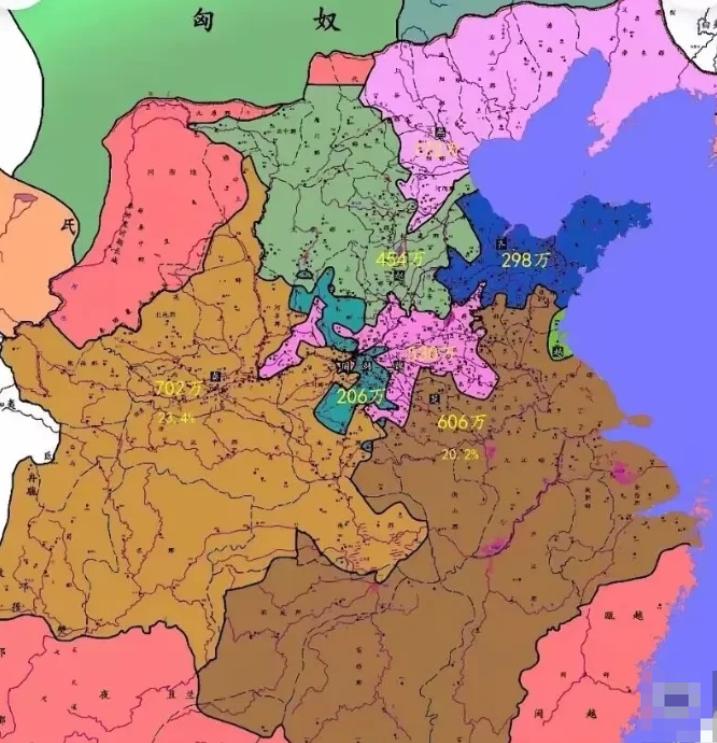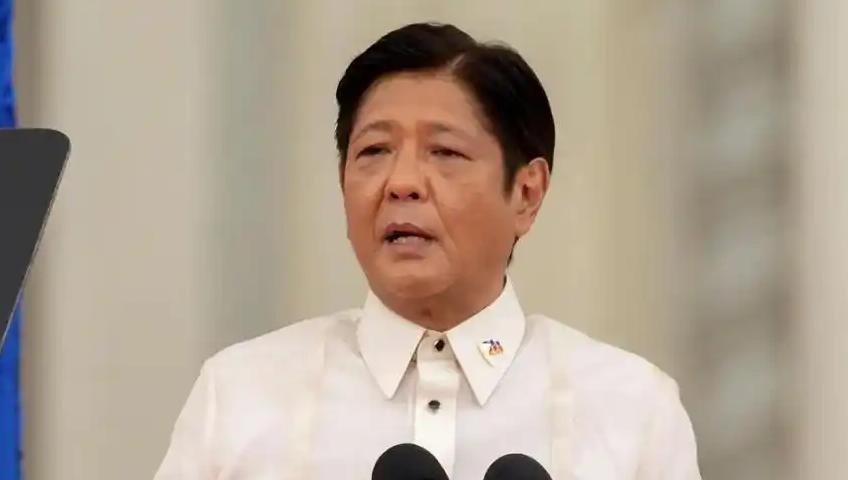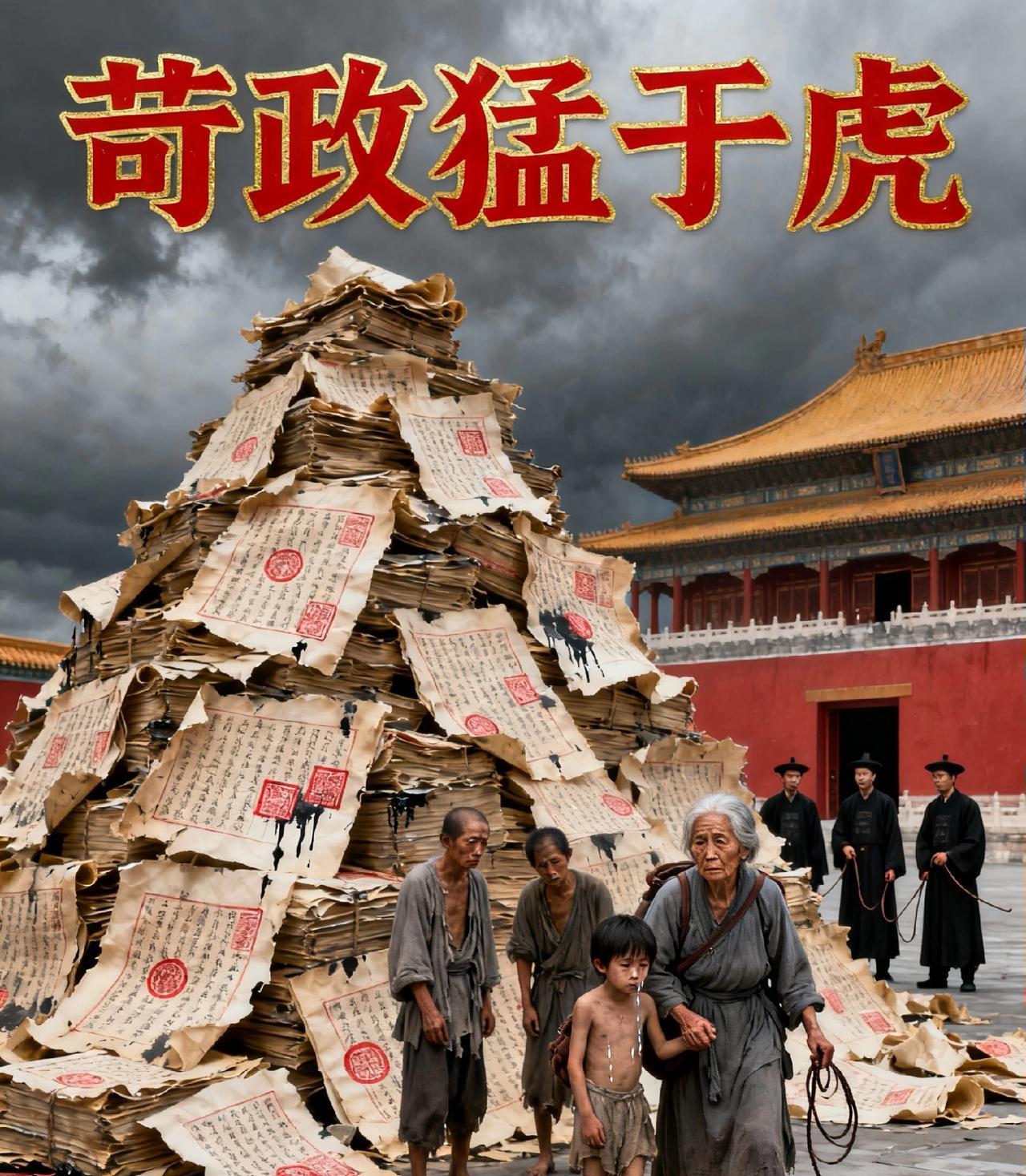1951年1月,83名志愿军阻击敌人1个团,打到后面只剩7人,子弹全打光了,这时,19岁的司号员郑起掏出军号一吹,敌人居然扭头就跑。 这事儿听着像传奇,却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战斗。故事要从三天前的深夜说起。 1951 年 1 月 1 日夜里,天特别黑。郑起所在的 39 军 116 师 347 团 7 连接到命令,要插到釜谷里去。 这个河南小伙子攥着那把从日军手里缴来的铜号,跟在连长厉凤堂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走。雪没到膝盖,棉裤冻得硬邦邦,没人吭声。 大家都清楚,釜谷里是英军第 29 旅南逃的唯一通道,必须卡住这儿。 “小心警戒!” 厉凤堂的声音压得很低。借着点月光,郑起看见前面土坡上有几个黑影在动。 “是英军哨兵!” 他刚要开口,就听见 “咔嚓” 一声 —— 副班长王二柱把步枪保险打开了。 “别开枪!” 厉凤堂赶紧按住他的枪管,“用刺刀解决!” 月光下,12 个志愿军战士扑过去。这场突袭让 7 连成功控制了釜谷里的关键位置,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占了釜谷里,7 连立刻动手挖工事。郑起把最后一颗反坦克地雷埋进土里,就听见远处传来 “轰隆轰隆” 的机器声。 “敌人来了!” 他抄起军号想吹,被厉凤堂按住:“先别吹,等近了再动手,省点劲。” 早上 9 点整,英军的炮弹准时砸过来。郑起缩在防炮洞里,感觉地都在晃。 从射击孔往外看,三辆 “百人队长” 坦克正碾过雷区。 “打履带!” 厉凤堂大喊。火箭筒手李有才扣扳机,发现发射管早被弹片砸弯了,根本用不了。 “用集束手榴弹!” 郑起抓了五颗手榴弹就要冲,厉凤堂一把拉住他:“你是司号员,得留着命吹冲锋号!” 话音刚落,一颗迫击炮弹在战壕里炸开。厉凤堂被气浪掀起来,胸前的望远镜碎成了渣。连长的牺牲让阵地上的气氛瞬间凝重,也把更重的担子压在了剩下的战士肩上。 郑起在碎土里找到厉凤堂时,老连长的肠子已经流到雪地上了。 “郑起……” 厉凤堂喘着气,把驳壳枪塞给他,“阵地…… 给你了……” 这时候,阵地上就剩 17 个能打的战士,子弹也没多少了。郑起把最后两箱手榴弹分给大家。 看见副指导员张鼎的钢盔被削掉一半,头骨都露出来了,还在端着机枪扫。 “老张!” 他刚要跑过去,张鼎身子一仰倒在地上,机枪还在冒烟。 下午 3 点,英军第六次冲上来。郑起趴在战壕里,看敌人的钢盔一片一片地涌过来。 “省着点子弹!” 他喊完,战士们的枪响得很齐。 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郑起抓起块冻硬的石头朝敌人砸,就见一个英军士兵的刺刀已经快到眼前了。第六次冲锋被勉强打退,但战士们也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而敌人的进攻还在继续。 1 月 3 日傍晚,阵地上就剩下 7 个人了。郑起摸了摸腰上的军号,铜号身被体温焐得暖暖的。 英军第七次进攻开始,6 辆坦克排着三角队形在前头,步兵猫着腰跟在后面。 “准备拼刺刀!” 郑起喊了一声,战士们 “唰” 地站起来,刺刀亮得晃眼。 20 米,15 米,10 米…… 眼看能看清敌人的脸了,郑起突然举起军号。 “滴滴答滴滴滴 ——” 冲锋号声一下子传开,把山上的乌鸦都惊飞了。 正在往前冲的英军士兵,听见号声都停住了,端枪的手开始抖。 “他们要反攻了!” 一个英军少尉尖叫着转身就跑,钢盔掉了都没捡。 再远些,坦克的炮塔开始转,履带 “嘎吱嘎吱” 响着往后退 —— 他们居然在撤退!谁也没想到, 这把军号成了扭转战局的关键,让濒临绝境的志愿军战士守住了阵地。 三天后,志愿军大部队赶到时,釜谷里的雪地上全是弹坑和尸体。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在英军指挥所发现份没发出去的电报,上面写着:“共军的军号有魔力,听见的人没有不害怕的……” 这场仗,7 连用 83 个人挡住英军一个团,打死打伤 450 多个敌人,缴了 3 辆坦克、8 门炮。 郑起因吹号退敌,被评上 “二级战斗英雄”,记特等功。 1951 年 10 月,他作为英模代表回北京参加国庆,在中南海见毛主席时,那把带血的军号就别在腰上。 现在,这把军号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玻璃柜子前,常有些头发白了的老兵站着看,眼里会流泪。 郑起退休后,常去各地讲这段事,每次都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能耐,是志愿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把敌人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