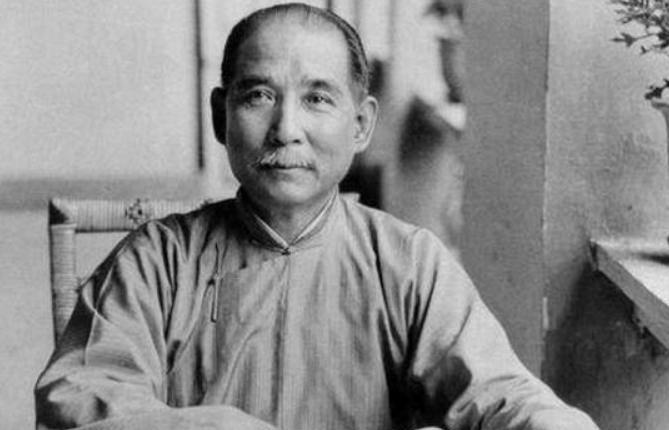50年毛主席深夜发电找一位73岁老教师,找到后,毛主席:立即枪决 “谭余保同志,马上帮我把罗克绍挖出来。”1950年11月下旬的深夜,毛主席在中南海低声开口,时针已指向两点。窗外树影恍惚,屋内案头灯火通明,文件摞成小山,他却仍保持清醒。对他而言,国家的晨曦刚刚出现,任何细节都不能被忽略,哪怕是距今二十多年的一桩旧案。 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百废待兴: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哪一件不是生死大事?可就在这个档口,毛主席突然想起井冈山时期那支嚣张的茶陵民团。那支民团的头目罗克绍,当年数次伏击红军,几乎断送了秋收起义余部的生路。此仇未忘,此人未除,总像一根倒刺扎在指尖。毛主席合上卷宗时,一张泛黄的旧名单压在最上层,罗克绍的名字赫然在列。于是,急电飞向长沙。 电报被送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值班室时,副主席谭余保刚换下外衣准备合眼。看到落款“毛泽东”,他精神一震。谭余保同样出自井冈山,根据地的血雨腥风他最清楚。短暂的沉默后,他简单嘱咐一句:“调档,派人,今晚动身。”不需要解释,所有在场干部都明白事情的分量。 罗克绍当时隐匿在茶陵县江口乡,表面身份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73岁,高瘦,带着老花镜教算术,外人看来不过是个皤然老人。可资历稍老的群众见到他仍会躲闪——他们记得,当年罗克绍“脚踏七寸枪”,带着民团烧屋子、绑壮丁。土地革命时期,革命者夜里刻意绕开那片稻田,就是怕撞见他。 搜捕组赶到茶陵后,得到的第一手消息却十分蹊跷:罗克绍“突发重病”,并已下葬。棺材埋在后山,墓碑新泥尚湿。一个73岁的老人突然暴毙?领先经验的老干警眉头皱紧。为了确认,他留下一句玩笑,“死人会喘气吗,咱得亲自看看。”随后暗中盯住罗家动向。 接下来数日,他发现罗妻及长子凌晨拎着饭盒往山里钻,一去一回,行动诡秘。第五天夜里,山洞口亮起油灯,一个黑影正在翻报纸。干警趁其弯腰,手电一晃:“不许动!”罗克绍束手,被带回茶陵县城。当年名震一方的民团头子,此刻佝偻如囚。 捕人电报转回长沙,谭余保在电话里只说了八个字:“已获,听候中央处理。”几小时后,中央批示到达:逮捕,公审,枪决。执行地点选在株洲郊外旧军营,公开宣判那天,冷雨如丝。罗克绍站在台上,神情木然。主持审判的检察员列举罪行:焚毁农户十二处,枪杀贫农二十六名,围堵红军后勤队三次。证人上前指认,证据逐条摆出,罗克绍无言。宣判书念完,场内只有雨声。押赴刑场时,他嘀咕一句,“早知如此,不如下手更狠。”这句话被值勤战士如实记录在案。 为什么要追究一个七旬老人的旧账?许多人私下议论。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新政权要立威,也要立法。井冈山时期,罗克绍所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地方豪绅与反动武装的合流,专门针对农民协会和赤卫队。若此人苟且偷生,基层百姓会疑惑:人民政府是否真的维护正义?更深层的考量在于,建立秩序必须让过往的血债有清算、有结论。否则,握着枪奔赴战场的无数战士该向谁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并非简单以“私怨”行事。1950年秋,他已批示多起“宽大处理”案例——凡属无大恶、自动悔改者,多给出路。罗克绍不同,他在解放前夕交出财产,摇身一变进了学校,看似“改过自新”,实则潜藏。茶陵群众仍惧其威名,这说明他并未真正放下过去。再加上检察机关调查确认,他参与过多笔血案,且从未自首,结局便无回旋余地。 枪声响过,罗克绍案尘埃落定。株洲雨停,空旷的操场只剩硝烟味道。湖南省公安厅随后发布通报,用词克制,不见夸张:“罗克绍,罪证确凿,依法处决。”纸面上短短一行,却告诉外界一个道理:新中国的法律威严,不因年岁,不因身份而打折。 事件过去多年,再读档案,我依旧对那封深夜电报印象深刻。毛主席工作堆积如山,却抽出时间点名一个小县老匪,是因为他深知基层秩序比纸上蓝图更重要。政权之稳,始于百姓心安;百姓心安,则需公正可见。罗克绍案给湖南绅霸势力敲响警钟,也让刚踏入和平年代的干部明白一件事:斗争还未结束,只是换了舞台。 有人问,若罗克绍真在1950年彻底改悔,结果会不会不同?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悔改首先是主动坦白,而不是用假死掩饰罪责。当他决定躲进山洞的那一刻,审判就已经到来。 茶陵的冬夜很冷。当年的搜捕老干警晚年提起此事,只淡淡一句:“抓到他后,我睡了三天囫囵觉。”无须豪言,事实本身已说明一切。 罗克绍走了,茶陵小学依旧上课铃响,孩子们背着新课本往教室跑。历史车轮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