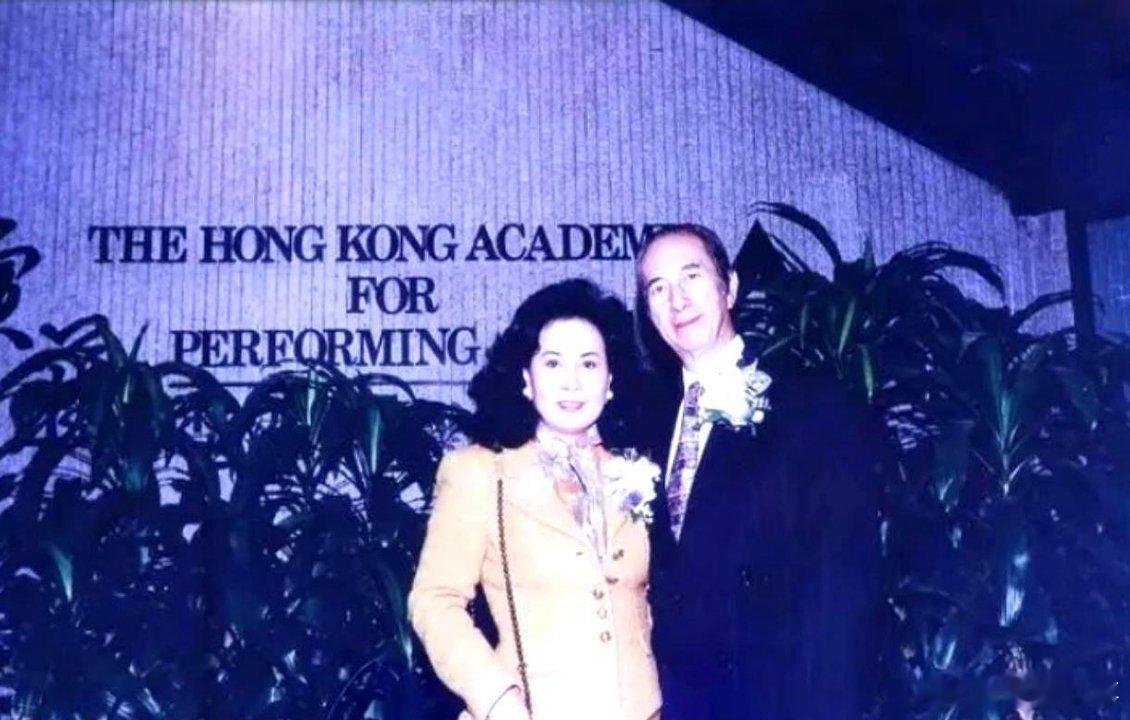影帝梁家辉曾经在节目上谈到爱国情结,他毫不留情表示 “我觉得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这种 “缺乏” 并非天生的遗忘,而是殖民统治精心编织的认知牢笼。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的学校开始推行 “去中国化” 教育:课本里,中国历史被拆解为 “远东史” 的附录,林则徐成了 “破坏中英贸易的罪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被描述为 “暴力骚乱”。
1920 年代的香港大学,中文课仅作为选修课存在,考试内容多取自西方文学,学生能流利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却未必能读懂《论语》中的 “己所不欲”。 街头的空间符号更在强化这种割裂。皇后大道的路牌用英文标注 “Queen's Road”,尖沙咀的钟楼刻着 “1910”—— 那是英国殖民者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而建。
1950 年代的中环,汇丰银行大厦前的铜狮子瞪着黄浦江方向,门口的印度警卫对华人进出盘查格外严格,而英国人却能直接通行。
梁家辉童年时随父亲去码头,看到华工扛着货物经过 “欧洲人专用通道” 时必须低头,否则会被殖民者的皮鞭抽打,那种 “二等公民” 的屈辱,成了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但文化的根须总在缝隙中生长。1940 年代的铜锣湾,粤剧戏班仍在演出《帝女花》,台下观众跟着哼唱 “落花满天蔽月光” 时,有人悄悄抹去眼角的泪 —— 那是对家国命运的隐喻。
春节时,即使殖民当局限制燃放鞭炮,香港人仍会在凌晨偷偷点燃一挂小炮仗,听那声脆响,仿佛能与千里之外的故乡呼应。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油麻地的华人商铺自发挂起红灯笼,虽不敢亮出五星红旗,却用 “庆祝新岁” 的幌子,传递着对祖国新生的隐秘期待。 这种矛盾在 1960 年代达到顶峰。
一方面,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成了殖民者口中的 “东方之珠”,年轻人以说流利英文、穿西装为时尚;另一方面,内地的 “文化大革命” 消息通过走私报纸传入,引发部分香港人对 “祖国” 的恐惧与疏离。
梁家辉那时在 TVB 当训练生,剧组里,英国导演要求把古装剧里的 “中国龙” 图案改小,理由是 “避免冒犯王室”,而老演员们私下里仍会教新人唱《黄河大合唱》的片段,唱到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时,声音总是格外响亮。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香港的认知湖面。
中环的股票交易所里,商人热议着 “九七后” 的投资风险;茶餐厅里,老人用粤语争论 “回归后会不会要改说普通话”;学校的历史课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中国地图,老师第一次在黑板上写下 “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下学生的眼神里,有困惑,更有一丝茫然的期待。
梁家辉那年拍《火烧圆明园》,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取景地,他望着烟波致爽殿的匾额,突然对导演说:“原来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这么辉煌的文明。” 回归前的几年,香港街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书店里,《中国大百科全书》开始畅销;电台播放的粤语歌曲里,出现了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的歌词;1996 年,香港少年合唱团首次到北京演出,演唱《歌唱祖国》时,台下观众的掌声持续了五分钟。
有位老教师在日记里写:“教了四十年书,第一次敢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你们是中国人。”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五星红旗在会展中心升起时,梁家辉站在人群中,看着米字旗缓缓降下。
他后来回忆,那一刻没有激动的欢呼,更多人是沉默的,仿佛在消化一段被扭曲的历史。身边的年轻人拿出相机拍照,老人则对着国旗行注目礼,有人低声说:“终于回家了。” 这种 “回家” 的认知重建,在回归后逐渐加速。
中小学开始推行 “国民教育” 课程,学生要学习《基本法》,参加 “认识祖国” 夏令营;2008 年北京奥运会,香港街头的五星红旗比紫荆花旗还要多;2019 年,面对乱港分子的破坏,无数香港市民自发组成 “守护国旗” 队伍,用身体筑起人墙。
梁家辉在一次访谈中展示女儿的课本,里面有整整一章讲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插图里,港珠澳大桥像一条巨龙,连接着香港与珠海、澳门。 那些曾经 “缺乏的概念”,正在被亲身经历填满。香港青年到深圳创业,用微信支付结算;老人通过高铁去内地探亲,感叹 “三个小时就到广州”;孩子们在历史课上知道了鸦片战争的真相,明白香港的被殖民是国家的屈辱。 维多利亚港的海浪拍打着堤岸,一百多年来从未改变。只是如今,岸边的建筑上,“中国香港” 的字样格外醒目。
那些曾经被割裂的记忆,正在重新拼凑成完整的图景:香港不是孤立的岛屿,而是中国版图上的一颗明珠,它的历史,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