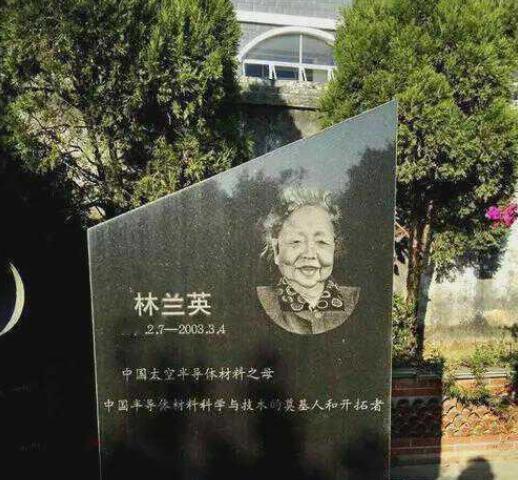1957年,美国海关私吞了一位中国女人行李箱里面的6800美金,但她却开心地笑了。殊不知美国海关的这一行为,导致美国重大损失…… 1957年的冬天,纽约港口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 林兰英攥着衣角站在海关检查台前,看着工作人员把一沓支票塞进抽屉,那是她在美国八年攒下的6800美元。 她脸上装作急得发红,手却悄悄按了按大衣内袋,那里藏着两个小药瓶,瓶底沉着的锗和硅单晶,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细碎的光。 这不是她第一次为了读书和命运较劲。 七岁那年,莆田老家的灶台前,她踩着小板凳刷碗,听着母亲跟邻居说"女娃认字有啥用",当晚就把自己关在柴房。 三天后母亲掀开柴门,看见瘦得脱了形的女儿手里还攥着捡来的旧书页,终于松了口:"要读可以,晨起烧饭、傍晚喂猪,一样不能少。" 从此,天没亮她就蹲在灶台前生火,火苗舔着锅底,她借着光背算术题,手指冻得握不住筷子,就往热水里蘸一蘸接着算。 1948年秋天,狄金森学院的教授把助学金申请表推到她面前时,她刚在福建协和大学教完最后一堂课。 出国的邮轮上,她把唯一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全是物理课本。在美国的课堂上,她总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比谁都密。 有次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难题,她盯着看了十分钟,突然快步走上前,用粉笔划出解题思路,粉笔灰落在深蓝色旗袍上,像落了层细雪。 后来转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她听说半导体是未来的方向,硬是把数学系的课本换成了物理系的,导师劝她"数学领域你已经快摸到天花板了",她只说:"祖国将来用得上半导体。" 在索菲尼亚公司的实验室里,她第一次见到硅单晶的拉制过程。技术员反复调试设备,晶体却总在最后一步碎裂。 她站在观察窗前看了三天,突然指着熔炉说:"加个籽晶罩试试。" 当第一根完整的硅单晶从炉子里取出来时,同事们欢呼着拥抱她,她却悄悄把一小块碎晶收进了口袋。 那时她的年薪已经涨到一万美元,这足够买下纽约郊区的一栋小别墅,但每个月发工资,她都把大半换成汇票寄回国,汇票附言里总写着"等我回去"。 1956年夏天,国内寄来的信在抽屉里放了三天。 信纸边缘被她摸得发卷,"祖国需要你"五个字像烙铁一样烫。 她去移民局申请回国,办事员翻着她的档案笑:"留在美国,你母亲能住最好的医院。" 她没说话,转身就去订船票。老板把续约合同摆在她面前,数字后面加了好几个零,她提笔在上面划了个叉。 那些日子,她和其他想回国的学者常聚在唐人街的茶馆里,有人说"美国不放人怎么办",她掏出偷偷攒下的晶体碎片:"就算走路,我也要把这些带回去。" 登船前的检查比想象中严格。 海关人员把她的行李箱翻了个底朝天,衬衫被抖得皱巴巴的,书本散了一地。 当那两个药瓶从大衣口袋滑出来时,林兰英的心跳得像擂鼓。 她看着工作人员的目光被桌上的支票吸走,听着他们说"这些钱要没收",悄悄把药瓶往脚边挪了挪。 踏上甲板的那一刻,她摸了摸内袋,晶体隔着布料硌着心口,像揣着两颗滚烫的星。 回国的邮轮走了一个月。 她在船舱里把晶体包了又包,用软布裹了三层。 有次风浪太大,药瓶从枕头下滚出来,她扑过去接住,手心被玻璃边缘硌出红印也没察觉。 靠岸那天,她攥着药瓶下船,江风掀起她的衣角,她抬头望着码头的红旗,突然笑了,眼里的光比晶体还亮。 到中科院报到的第二天,她就带着晶体进了实验室。 那时的实验室连恒温设备都没有,她把自己的棉大衣拆了,给仪器做了个保温套。 深夜的实验室里,只有她的工作台亮着灯,显微镜下,锗单晶在高温下慢慢延展,像初春解冻的河流。 半年后,当第一根国产锗单晶从炉子里取出来时,她摸了摸晶体表面,眼泪突然掉在上面,晕开一小片水渍。 1958年国庆前,她带着团队攻克了硅单晶技术。 那天,北京电子管厂用他们做的材料造出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滋滋的电流声里,传出播音员清亮的声音。 她站在人群里听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在莆田老家,自己蹲在灶台前背课文的夜晚。 那时的她一定想不到,当年拼死要读书的姑娘,会在多年后,让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后来的日子里,她总在实验室待到深夜。 有人劝她歇歇,她指着培养皿里的砷化镓晶体说:"这些小家伙不等人。" 1987年,当卫星带着她的实验舱升空时,她守在屏幕前,看着数据一点点传回来,突然想起1957年那个冬天,自己在海关前攥紧衣角的瞬间。 原来有些种子,从被埋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长成参天大树。 她在美国住的宿舍墙上,一直挂着张世界地图。 地图上,纽约和北京之间被人用红笔画了条直线,线的尽头,写着两个小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