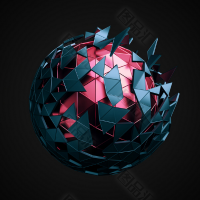香港为何总对内陆人有偏见?影帝梁家辉道出真相:“香港人其实挺可悲的,被英国人统治了一百多年,在回归以前,我们这一辈人很缺乏对祖国的概念……” 梁家辉说这话时,正在录一档访谈节目,手里捏着个喝空的茶杯,指节泛白。
他那年58岁,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太多故事——1983年他凭《垂帘听政》拿金像奖影帝,却因为拒绝跟英资公司签约,被封杀整整四年,只能去街边摆摊卖首饰。
那会儿有英国警察盘查他,看他身份证上写着“英国属土公民”,眼神里的轻蔑像针一样扎人。 他不是没试过了解“祖国”。
上小学时,课本里讲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功绩,画的是米字旗飘扬的港口,中国历史被压缩成几页“远东古代文明”,连鸦片战争都被写成“贸易冲突”。有次他问老师“长城什么样”,被训斥“上课不要想无关的事”。
直到17岁,他在电影院看了部内地纪录片,镜头扫过天安门广场,他才第一次对着屏幕里的五星红旗发愣:“原来那就是祖国的样子。” 偏见的根,早被殖民统治埋进了日子里。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内陆人被叫做“阿灿”,这个词来自电视剧里一个穿的确良衬衫、不懂电梯按钮的角色,带着天然的嘲讽。
梁家辉在菜市场见过,卖鱼佬对着讲普通话的顾客故意抬高价格,说“他们钱好赚”;
邻居阿姨看见内陆来的保姆,总会把首饰盒锁得紧紧的,念叨“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没人想过,那些挤在罗湖桥头、背着蛇皮袋的人,多数是为了给家里赚点救命钱,就像当年逃到香港讨生活的祖辈。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香港街头开始挂起倒计时牌。
梁家辉去北京拍电影,第一次坐火车穿过罗湖桥,乘务员用带着京腔的普通话说“欢迎回家”,他突然红了眼眶。剧组里的内地演员拉着他去吃涮羊肉,热气腾腾的铜锅里,有人给他夹起一片毛肚,
说“咱们都是中国人,别客气”。
那天他喝了不少二锅头,晕乎乎地站在长安街,看着路灯连成的光带,突然懂了“祖国”不是课本里的词,是有人会笑着给你递筷子,是街头小贩跟你讨价还价时的热乎气。 回归那天,他带着女儿去维港看烟花。小姑娘指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问“那是什么”,他蹲下来,把女儿的手放在自己手心里,说“那是咱们的国旗,以后你要记住”。
可身边有老人在哭,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去英国免签了”;有年轻人举着相机拍米字旗落下,嘴里嘟囔“习惯了的日子要变了”。梁家辉没说话,他知道,一百多年的隔阂,不是升一面旗就能抹平的。 这些年,偏见在慢慢变味。跨境电商火起来时,香港代购疯抢内陆的螺蛳粉,说“比进口零食好吃”;
疫情期间,内陆医疗队带着物资抵港,有香港市民举着“感谢祖国”的牌子在机场等了整夜。可照样有争执——地铁里因为“能不能吃东西”吵起来,商场里因为“排队加塞”红了脸。
有人说“是内陆人不懂规矩”,却忘了香港的“规矩”里,藏着太多殖民时期的烙印,比如靠左行、用英尺英寸,这些本就和内陆的生活习惯隔着代际。 梁家辉在节目里举过个例子:他带香港的朋友去西安看兵马俑,朋友盯着那些陶俑惊叹“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历史”,转头却问“这里的厕所干净吗”。
他说“你看,偏见就像一层雾,知道兵马俑厉害是拨开了一小角,觉得厕所不干净,是还没走到雾后面去”。 说到底,偏见的本质是陌生。
英国统治时,刻意切断香港与内陆的脐带,让几代人在“英国属土”的身份里打转,既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也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回归后,口岸通了,高铁开了,可真正的理解,需要的不是一张车票,是愿意放下预设,听对方讲句“我小时候也爱吃奶奶做的红烧肉”,是明白“不一样”不等于“不好”。 梁家辉现在常带孙子去深圳逛公园,小家伙会跟内陆的小朋友抢滑梯,会奶声奶气地说“我爷爷是中国人,你也是”。他说“这代孩子不用像我们,对着地图猜祖国的样子”。 可那些没来得及被时间磨平的隔阂,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心思,真的能被孩子的笑声吹散吗?或许偏见从来不是谁的错,只是历史留下的褶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用走过去的勇气,一点点熨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