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六年,17岁的纪晓岚迎娶大自己3岁的马月芳,新婚初夜,纪晓岚正准备掀开盖头,一睹马月芳的芳容时,马月芳竟突然躲开,不愿圆房,但和纪晓岚一番对话后,她死心塌地跟了他56年。 乾隆大大六年那会儿,纪晓岚才十七岁的小鲜肉一枚,就娶了比他大三岁的马月芳。这马月芳啊,是内阁中书马永图的千金,打小就聪明绝顶,诗书啥的都不在话下,东光那块儿提起她,都说是个才女呢。 得说句实在的,纪晓岚那会儿虽说有才名,可终究是个半大孩子。他爹纪容舒是京官,家教严,他打小泡在书堆里,诗词歌赋张口就来,可论人情世故,还带着点愣头青的憨气。媒人提亲时,马家看中的是他的才气,马月芳自己呢,心里却打鼓——听说这纪家少爷嗜书如命,性子跳脱,怕是个不懂疼人的。 红烛摇影,新房里静得能听见烛花爆裂的声响。纪晓岚捏着盖头的一角,手心冒汗,刚要往上提,马月芳忽然往旁边挪了挪,盖头没掀成,倒带起一阵香风,是她发间的茉莉香。 “纪公子且慢。”马月芳的声音从盖头下传出来,清亮,带着点不容置疑的劲儿,“我有几句话想问,问明白了,再掀不迟。” 纪晓岚手停在半空,愣了愣。他见过的大家闺秀,要么娇羞不语,要么低眉顺目,像马月芳这样新婚夜“提条件”的,还是头一回见。他反倒来了兴致,收了手,笑道:“马姑娘请讲,只要我知道的,绝无隐瞒。” “听说公子三岁能背《论语》,七岁能作诗文,”盖头下的声音顿了顿,“可公子觉得,女子读那么多书,有用吗?” 这问题问得突然,纪晓岚眨了眨眼。那会儿的世道,女子无才便是德,马家让马月芳读书,本就是破例。他琢磨着,这姑娘怕是在为自己“有才”找个说法。 “怎么没用?”纪晓岚的声音亮起来,“《诗经》里‘窈窕淑女’,可不是只说长得好看。若胸无点墨,纵有美貌,也不过是花瓶一只。姑娘能诗善文,这是福气,是本事,比那些只会描眉画眼的强百倍。” 盖头下的人似乎僵了一下,又问:“那公子将来若做了官,会不会觉得我这‘老妻’碍事?毕竟,我比你大,又不是只会伺候人的。” 这话里带着点刺,也藏着点怕。马月芳比纪晓岚大三岁,又是才女,心里难免有份骄傲,也怕这份骄傲在婚姻里成了错处。 纪晓岚这次没笑,语气沉了沉:“姑娘说笑了。娶媳妇是过日子,又不是买件摆设。你大我三岁,懂得多,将来正好教我;你有才情,咱俩能聊到一块儿,总比对着个话不投机的强。至于‘碍事’——我纪昀这辈子,就怕身边人跟我没话说。” 他说得坦诚,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热烈,没半点敷衍。 新房里静了片刻,接着,盖头被一只纤纤玉手自己掀开了。 马月芳就坐在那儿,眉眼清秀,没施多少粉黛,眼里却亮得很,像盛着星光。她看着纪晓岚,忽然笑了,那笑容里,之前的戒备散了,只剩点羞赧和释然:“公子这话,我信了。” 那晚的圆房,没多少旖旎,倒像两个朋友坐下来,说了半宿的话。马月芳讲她读诗时的见解,纪晓岚说他背书闹的笑话,烛火燃到天明,两人竟没觉得困。 往后的日子,真应了纪晓岚的话。 马月芳从不是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宅妇人。纪晓岚在书房看书,她就坐在旁边做针线,偶尔搭一句“这篇注解不对”,总能说到点子上。有次纪晓岚写文章卡了壳,对着“关关雎鸠”发呆,马月芳端来一碗莲子羹,轻声说:“《诗经》讲的是人情,不是死理,你把自己放进那水边,就懂了。” 乾隆十九年,纪晓岚因事被贬新疆,一走就是三年。家里乱成一锅粥,是马月芳撑着,安抚老幼,打理家事,还每月给纪晓岚寄信,信里不说难处,只讲孩子的功课、院里的花开了,末了附一句“安心做事,家里有我”。纪晓岚在新疆写的诗,后来结集出版,多半是对着马月芳的信,一字一句憋出来的。 等纪晓岚回京,奉命主编《四库全书》,忙得脚不沾地,有时半个月不回家。马月芳就把他常读的书整理出来,按类目放好,又让人在书局旁边租了个小院,亲自下厨给他做爱吃的酱肘子,怕他熬坏了身子。编书时遇到争议,纪晓岚总说“回家问我夫人”,同僚们笑他“惧内”,他却得意:“我夫人懂的,比你们多。” 他们一辈子没吵过几次架,唯一的回嘴,是马月芳劝纪晓岚少抽烟。纪晓岚烟瘾大,人称“纪大烟袋”,马月芳说:“烟伤肺,你还要编书呢,得好好活着。”纪晓岚嘴上嘟囔“就抽一口”,却偷偷把烟杆截短了些。 嘉庆十年,马月芳走了,享年76岁。纪晓岚握着她的手,老泪纵横,说了句:“你等我会儿,我把剩下的稿子校完就来。” 那之后,纪晓岚像变了个人,烟抽得少了,话也少了,常坐在马月芳生前坐过的椅子上,对着空院子发呆。有人劝他再纳个妾,他摇头:“没人能跟我聊《诗经》了。” 信息来源:基于《清史稿·纪晓岚传》《阅微草堂笔记》及纪氏家族史料综合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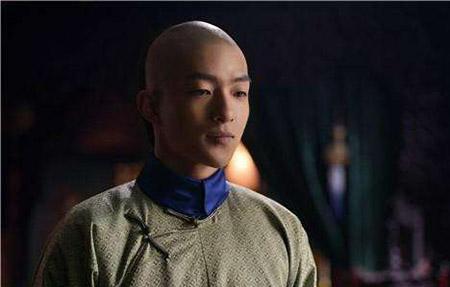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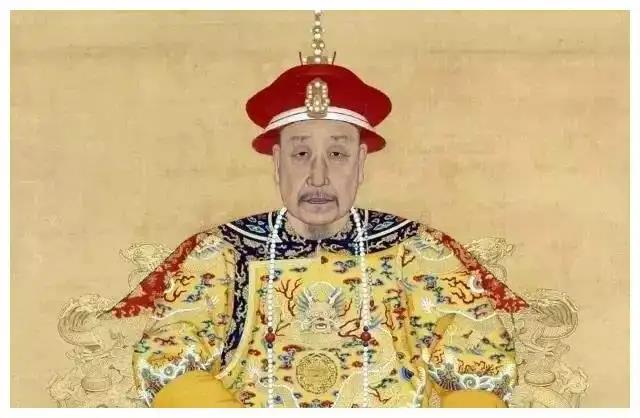

用户16xxx52
瞎编乱造,事实上纪晓岚哪方面特别厉害,一日不泄两眼冒火,夜驭几女不在话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