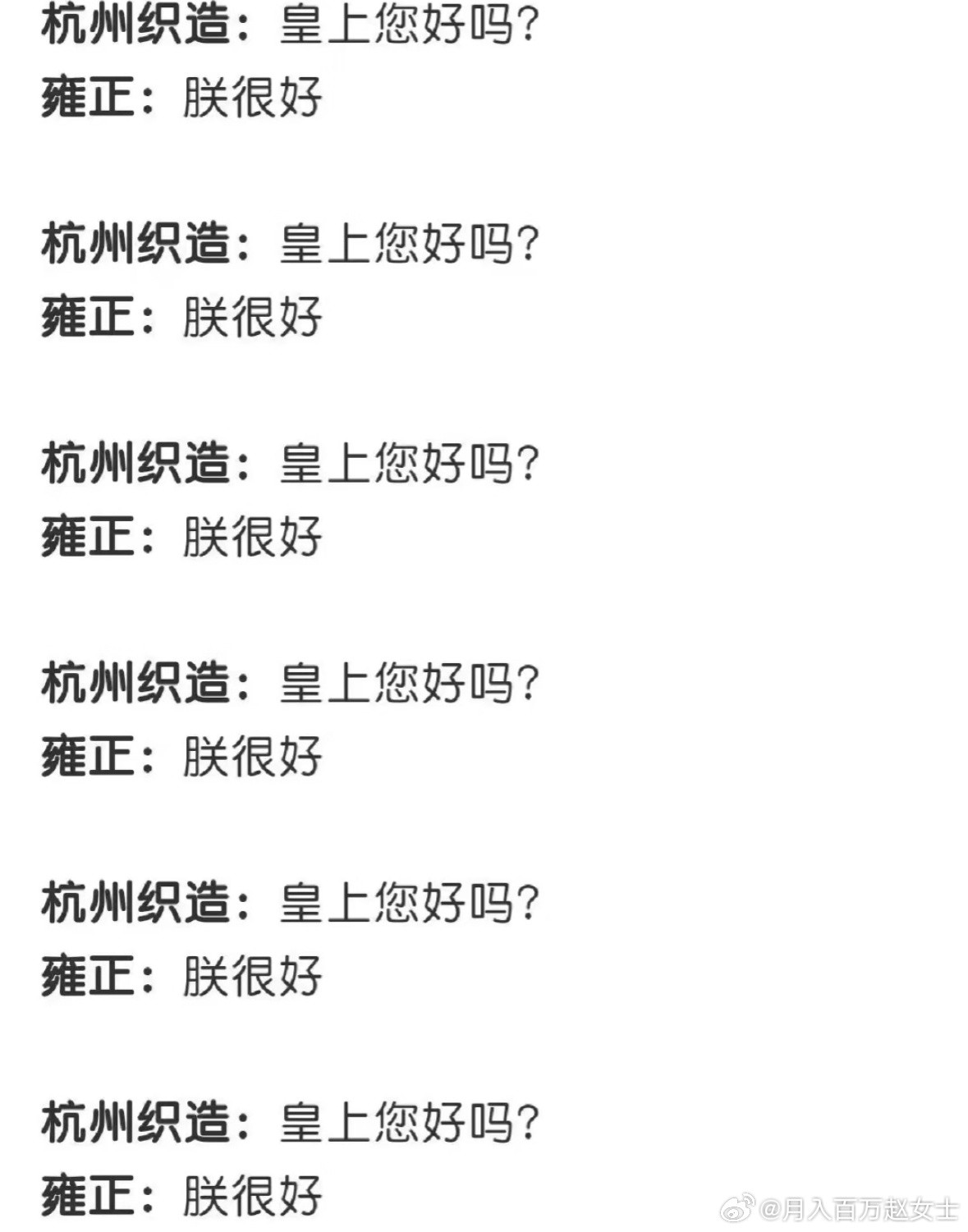唐僖宗时,皇宫里放出大量超过三十岁的宫女。有个才情出众的宫女嫁给了一个穷书生,婚后,宫女在丈夫房里发现一个箱子,打开一看,竟是自己的私有物品,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宫女唤作苏绾,在宫里待了整十二年。刚进宫时还是个梳双丫髻的小姑娘,跟着老嬷嬷学描花样子、填胭脂膏,后来被分到文书房抄录典籍,指尖常沾着松烟墨的香。三十岁这年宫门大开,她抱着个旧布包走出朱雀门,回头望时,见宫墙琉璃瓦在日头下闪得晃眼,倒没什么舍不得,只觉像褪了层紧裹的茧。 媒人领着她去见那穷书生时,她正在院角翻晒从宫里带出的几本诗集。书生叫柳砚,穿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衫,见了她倒不局促,只指着廊下晒的药草笑:“这是薄荷,天热时泡水解暑,你若住进来,我每日给你煎一碗。”苏绾瞧他案上堆着书稿,窗台上摆着盆快开花的兰草,心里便定了。 成婚第三日,苏绾替柳砚收拾屋子。他卧房里有个旧木箱,锁着却没拴牢。她本不是好奇的性子,偏那箱子角磨得发亮,看着比柳砚这破屋还年长些。 鬼使神差地掀开锁扣,里头铺着层褪色的青绸,上面摆着的东西让她指尖猛地一凉——那支缺了口的玉簪,是她十七岁生辰时,同屋姐姐偷偷塞给她的,后来在抄书时不慎掉在石阶上磕坏了,她心疼了好几日,随手丢在妆匣角落,离宫时竟忘了带。 还有那方绣着半朵山茶的丝帕,是她初学刺绣时的拙作,针脚歪歪扭扭,当年被掌事嬷嬷瞧见,笑她“绣得不如村妇”,她羞得连夜要烧,被文书房的老太监拦住,说“留着吧,往后看倒有趣”。 最让她心头发颤的是那页泛黄的诗笺,上面是她抄错的《春江花月夜》,“空里流霜不觉飞”抄成了“空里流霜不党飞”,当时急着交差没细看,后来在宫里再没找着,原以为早被当作废纸烧了。 柳砚推门进来时,正撞见苏绾捧着诗笺发怔。他脸“腾”地红了,手忙脚乱地想把箱子合上:“我……我不是故意的……”苏绾抬眼瞧他,见他耳尖红得像染了胭脂,倒比自己还慌。 “这些东西,你从哪儿得来的?”她声音有些发哑。 柳砚挠了挠头,蹲在她跟前慢慢说。他原是江南人,十岁那年随父亲来长安赶考,父亲染了急病,没等放榜就去了。他没钱葬父,文书房的刘太监见他可怜,让他在宫外卖些字画换钱,偶尔也托他给宫里的宫女带些宫外的新鲜玩意儿——比如糖糕铺子新做的梅花酥,或是书坊刚刻的话本。 “有回刘公公叫我去取些要丢的废纸,说里头或许有能练字的纸。”柳砚指尖划过那支玉簪,“我在纸堆里见着这簪子,玉虽不顶好,可瞧着磨得润润的,想着定是哪个姑娘常戴的,丢了该心疼,就偷偷收起来了。那帕子也是,夹在旧书里,山茶绣得虽不匀,可针脚紧,看得出绣时用了心。” 苏绾想起当年刘太监总爱拿些“废纸”给小杂役,有时是带墨痕的宣纸,有时是印错的书页。她那时只当是老人心善,给孩子们留些用度,从没想过里头还藏着这些。 “那这诗笺呢?”她捏着诗笺边缘,指腹蹭过那个错字。 “这是前年的事了。”柳砚声音低了些,“我在宫墙根下捡的,风刮得正紧,纸角都磨破了。上头的字……我瞧着好,不像宫里先生写的那样板正,带着点跳脱的劲儿。我总猜,写这字的姑娘,定是个心里透亮的人。”他顿了顿,抬头看她,眼里闪着光,“后来媒人说要给我介绍个从宫里出来的姑娘,叫苏绾,我还没见面就慌了——我总觉得,这些东西的主人,就是你。” 苏绾忽然想起,当年她总爱把抄废的诗笺揉成团扔出窗外,文书房窗外有棵老槐树,风一吹,纸团就顺着墙根滚。她也记起,有回托小杂役带话本,那孩子站在宫门外,眼睛亮得像落了星子,递话本时手指冻得通红,却还笑着说“姑娘要的《西厢记》,书坊刚补了页”。 她把诗笺放回箱子,盖好青绸。转身时见柳砚还蹲在地上,像个等着挨训的孩子。她伸手牵住他的手,他掌心有常年握笔磨出的茧,却暖得很。 “往后别锁了。”她轻声说,“这些东西,原就该和主人一处。” 柳砚抬头,见她眼里有光,比当年他捡诗笺时,长安的月光还亮。 其实这故事里藏着的,哪是些旧物件?是深宫高墙挡不住的人情。宫女们的一簪一帕,本是寻常物,可落在有心人眼里,就成了舍不得丢的念想。 柳砚捡的不是破烂,是那些被宫规磨得发钝的日子里,偷偷冒出来的活气——是十七岁姑娘对玉簪的疼惜,是初学刺绣时的羞赧,是抄错诗句时的慌忙。这些细碎的、带着温度的痕迹,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妥帖收着,等了十几年,终于回到主人身边。 都说宫里的人离了宫,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可苏绾的线,原来早被柳砚悄悄攥在手里了。那些她以为早被遗忘的瞬间,有人替她记着,这大概就是日子里最软的那部分了。 参考书籍:《唐宫词》(清·彭定求等编)、《唐代宫女生活考述》(黄正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