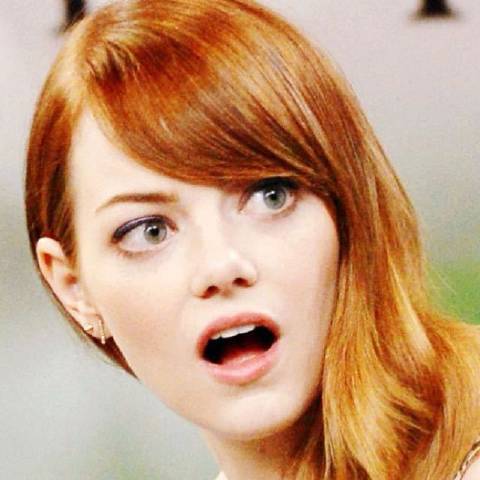张曼玉40岁时谈自己的演员生涯,这时她已息影。
「你们真觉得《青蛇》、《新龙门客栈》比《英雄》更出色?我确实钟爱《青蛇》中蛇化少女的角色设定,但成品最终令我失望。而《英雄》吸引我之处,在于它让我得以与武侠片作别,毕竟这类作品我已倾注足够心血,今后不会再涉足。
《英雄》之前,我拍的最后一部华语动作片是徐克的《青蛇》。那时候还在用威亚吊钢丝来表现飞檐走壁,仅是两个屋顶间的跳跃就需要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如今数字技术加持下,纵跃山峦易如反掌,这种技术进步反而解放了表演维度,让我们能更专注于内在表达。当年与成龙、杜琪峰、林岭东、徐克合作时,我并非现在的演员状态,未曾以严肃态度对待这类作品。而拍《英雄》时,我的感受完全不同,能够尝试更复杂的表演。
当年在香港一年高强度能拍十部电影,的确让我心力交瘁,但至少我认为它未曾摧毁我的艺术生命。在三十岁出头时,我感到迫切需要暂停一下,于是接演那部完全陌生的法国小制作《迷离劫》,只为逃离香港的疯狂节奏。此后我便大幅减产,只接拍真正渴望创作的作品。不过在那段高产岁月里,既有杰作诞生,也有作品纯粹是电影工业疯狂的产物。我们的电影当时风靡全亚洲,尤其在泰国、台湾、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明星名字如同品牌被买卖,影片像流水线产品般八天速成,我曾同时跨拍三部戏。若十年前没有减速,现在的我恐怕早已被彻底耗尽。
《2046》我试穿过服装,也试过妆。当时王家卫每次都会拍摄试镜素材。我本该在2003年8月和9月参与拍摄,10月初,王家卫还没准备好,我告诉他我得去拍《清洁》了。他让我再多留八天,我拒绝了。拍完《清洁》后,我再也不想回到《2046》的片场了,显然那部戏还没拍完。个人生活中有更需要优先处理的事务,希望他能理解。
当年我与他连续合作多部影片时,生活还没这么复杂。那时住在香港,我有充足的档期,能够接受他用整整一年时间即兴创作式地拍摄。但《花样年华》长达十五个月的拍摄周期确实严重影响了我的私人生活,我不愿再重蹈覆辙。虽然渴望能与王家卫再度合作,但如今的我已经不再年轻,不能再为电影牺牲个人生活,人生还有其他需要优先考虑的事。
在《清洁》之前,我的银幕形象从未如此贴近真实生活中的自己:淡妆、牛仔裤。里面我都是穿着自己的私服,只需在片场花五分钟补妆就能投入拍摄,这带来了一种真正的自由。而在《花样年华》的片场,妆发准备工作对我来说仿佛没有尽头。
《阮玲玉》在柏林获最佳女演员奖时,我正在马来西亚和成龙拍《警察故事3》,没能去领奖。那个奖让我挺开心的,但也就那样了。而这次凭借《清洁》获奖,我从影片展映开始就一直在戛纳,见证了它的反响。整个过程都很热烈,这个奖项是这四天精彩历程的美好收尾。
年轻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要演而优则唱,做什么影坛、歌坛双栖明星。做粤语流行乐没什么意义,除了金钱收益,但要付出巨大的自我牺牲。香港的音乐产业体系很糟糕,令人窒息,虽然在经济上实力雄厚,但在创作层面却十分匮乏,创意贫瘠,完全遵循快钱逻辑。流行歌手既不自己写歌,也不自己作曲,大多数人甚至也不会演奏乐器。只需穿着他人挑选的服装,终日穿梭于各类电视节目推销商品,不管什么节目都上。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个刚入行拍戏的年轻模特时,或许会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我的嗓音对这类音乐来说太奇怪了。而且我的喜好一直让我倾向于更摇滚、更个人化的东西。
无论我唱得好还是不好,那都是我的演唱方式,就这样……不是我害怕风险,大不了我会显得很可笑,我没花太多功夫,也没上过声乐课。
从经济层面看,市场正在复苏。五年前曾跌至谷底,但2000年初以来观影人次略有回升。核心问题在于八卦小报媒体,他们掌控着娱乐产业,利用年轻偶像女星作为报纸销量,又很快通过炮制隐私丑闻,批评她们的私生活来消费、消耗她们,对此几乎没有法律约束。导致年轻女演员越来越像一次性消费品。而电影工业本需要明星体系,我们既缺少娜奥米·沃茨这样专注作者电影的优秀演员,也缺乏茱莉亚·罗伯茨式的商业巨星。当下的香港电影两者皆失:既不给新人成长空间,也不让她们探索艺术方向。更何况现在行业只量产鬼片和动作喜剧,纵然有余力为、陈果等作者导演,他们的作品也难获反响,处境确实艰难。
当然也有出类拔萃的电影人,比如杜琪峰,他有点像新一代的徐克。但像吴宇森或徐克那样的电影,那种艺术水准如此之高的商业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后也再未出现过。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这也是我当年一年拍十二部电影的原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闪耀着星光,就像一场梦。如今,香港电影不过是一个乏味的产业,我在飞机上看那些新电影,总是一样的老套路,没有任何新意。
在巴黎,当街被认出时人们都很从容,顶多一句“看,是张曼玉“便继续交谈。巴黎上前问候的人会感谢我的艺术贡献,这与在香港公共场所遭遇的审视截然不同。能从人们的眼神里读到“她好丑,她好胖,她老了,她长痘痘了”,人们会抨击演员,仿佛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财富、名气付出代价。
如今,我把精力放在另一件事上,中国的教育,而这件事的成果我这辈子很可能都看不到。在中国大陆,很多20到40岁的农村人从来没上过学。我组织慈善义卖,对接企业募资筹集资金,我们已经在中国偏远农村援建了三所学校。我尤其关注女孩的教育问题,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比男孩还要低,贫困家庭往往会优先选择让男孩上学,而不是女孩。这种基于男性主导的文化传统若不改变,如果女孩没有机会上学接受教育,现状就永难改善。
我会定期前往中国的农村。很多中国人平静地生活在村里,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飞速变化,经济在快速发展。大多数村民没有为如此迅猛的变革做好准备,这种脱节令人忧心。四季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多数人仍对全球经济规则一无所知。必须传递这些知识工具,才能让经济发展在健康条件下实现,而现状显然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