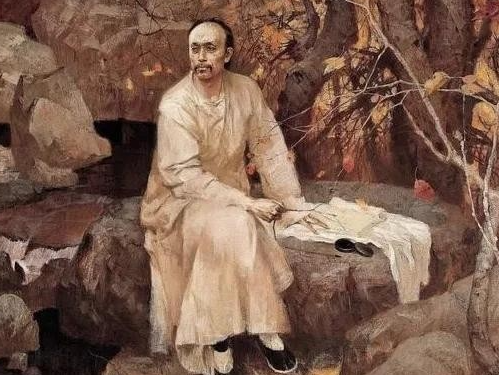1178年,在羊毛堆之中,成吉思汗与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发生了关系,而这是蒙古族最高的待客礼仪——遇客婚,没想到,在这之后,成吉思汗后来真的回来找这个小姑娘,可惜这个姑娘已经有了家室。 我在曾外祖母合答安的旧物箱里,摸到块硬邦邦的东西。 那是件褪成米白色的羊毛背心,针脚歪歪扭扭,领口处磨出了毛边。 指尖探进夹层时,触到两片叠在一起的毡片,青灰色的布面上,蓝线绣的羊群在昏暗的光线下微微发亮。 “这是你曾外祖父成吉思汗的信物。” 祖母用骨梳蘸着酥油,给我梳辫子时说,“1178年的夏天,他就躲在这样的羊毛堆里。” 那年曾外祖母刚满十一岁,正蹲在泰赤乌部的牧场里,给部落首领准备做祭袍的羊毛。 她父亲是部落里的放羊奴隶,前几日暴雨冲垮了羊圈,一家人正愁着赔偿损失。 忽然从灌木丛里滚出个满身是伤的少年,皮靴上还沾着暗红的血渍。 “他举着弯刀问见没见穿灰袍的少年,你曾外祖母往羊群那边一指,说骑着黑马跑了。” 祖母的梳齿划过我的发梢,“其实那少年就藏在羊毛堆里,睫毛上还挂着毛絮呢。” 我摩挲着毡片上的红点,那颜色深得像干涸的血。 祖母说,那是曾外祖母被针扎破的指尖染上去的。 当晚按照草原“遇客婚”的习俗,少年在他们家的蒙古包过夜,临走时说,若能活着回来,定会娶她为妻。 “你曾外祖母连夜缝了这两块毡片,”祖母指着毡片上的羊群,“一片给他当信物,一片自己留着。” 少年走后的第八年,曾外祖母嫁给了邻帐的牧民巴图。 那时她已经能织出最细密的羊毛毯,每次赶集会,巴图总会用木碗换串糖葫芦给她。 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三岁那年,巴图去山北换盐,再也没回来。 “后来才知道,是被成吉思汗的部下误杀了。” 祖母的梳齿顿了顿,“1206年他在斡难河源头称大汗时,还在派怯薛军四处找她。” 毡片的边角磨得发亮,能看出被反复摩挲的痕迹。 祖母说,成吉思汗带着这片毡片打了无数场仗,从塔塔尔部打到乃蛮部,每次快撑不住时,就摸一摸上面的羊群。 找到曾外祖母的那天,她正在戈壁边缘的毡房前晒羊毛。 银白的发丝沾着雪粒,手里的纺锤突然掉在地上,羊毛线缠了满脚。 成吉思汗举着毡片站在她面前,两鬓已经有了白霜:“我找了你十八年。” “他把两块毡片叠在一起时,两个红点正好重合。” 祖母把梳好的辫子盘在我头顶,“就像两群失散的羊终于碰面。” 曾外祖母住进汗宫后,总在西帐纺线。 成吉思汗处理完政务,就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看她把雪白的羊毛捻成线。 有次他指着窗外的羊群说:“泰赤乌部进贡的羊毛,不如你当年织的暖和。” 我展开背心的里衬,发现上面绣着辆小小的羊毛车。 祖母说,那是曾外祖母后来织上去的,1226年成吉思汗征讨西夏前,她特意在袍子里缝了个暗袋,把两块毡片放进去。 “她说就像当年藏在羊毛堆里那样安全。”祖母的声音轻下来,“可他再也没回来。” 毡片的边缘还粘着几根细羊毛,我放在鼻尖闻了闻,仿佛能嗅到1178年夏天的阳光味。 祖母说,成吉思汗的灵柩里,就放着这两块拼在一起的毡片,还有曾外祖母织的羊毛车纹样。 “草原上的‘遇客婚’习俗,就这样藏在针脚里。” 她把背心叠好,放回旧物箱,“有些承诺,比黄金还经得住岁月磨。” 我摸着发烫的耳垂走出帐篷,天边的晚霞正染红草原。 远处的羊群像流动的白云,恍惚间,仿佛看到1178年的羊毛堆里,少年和少女的影子正慢慢重叠,蓝线绣的羊群在他们脚下,连成了一片海。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