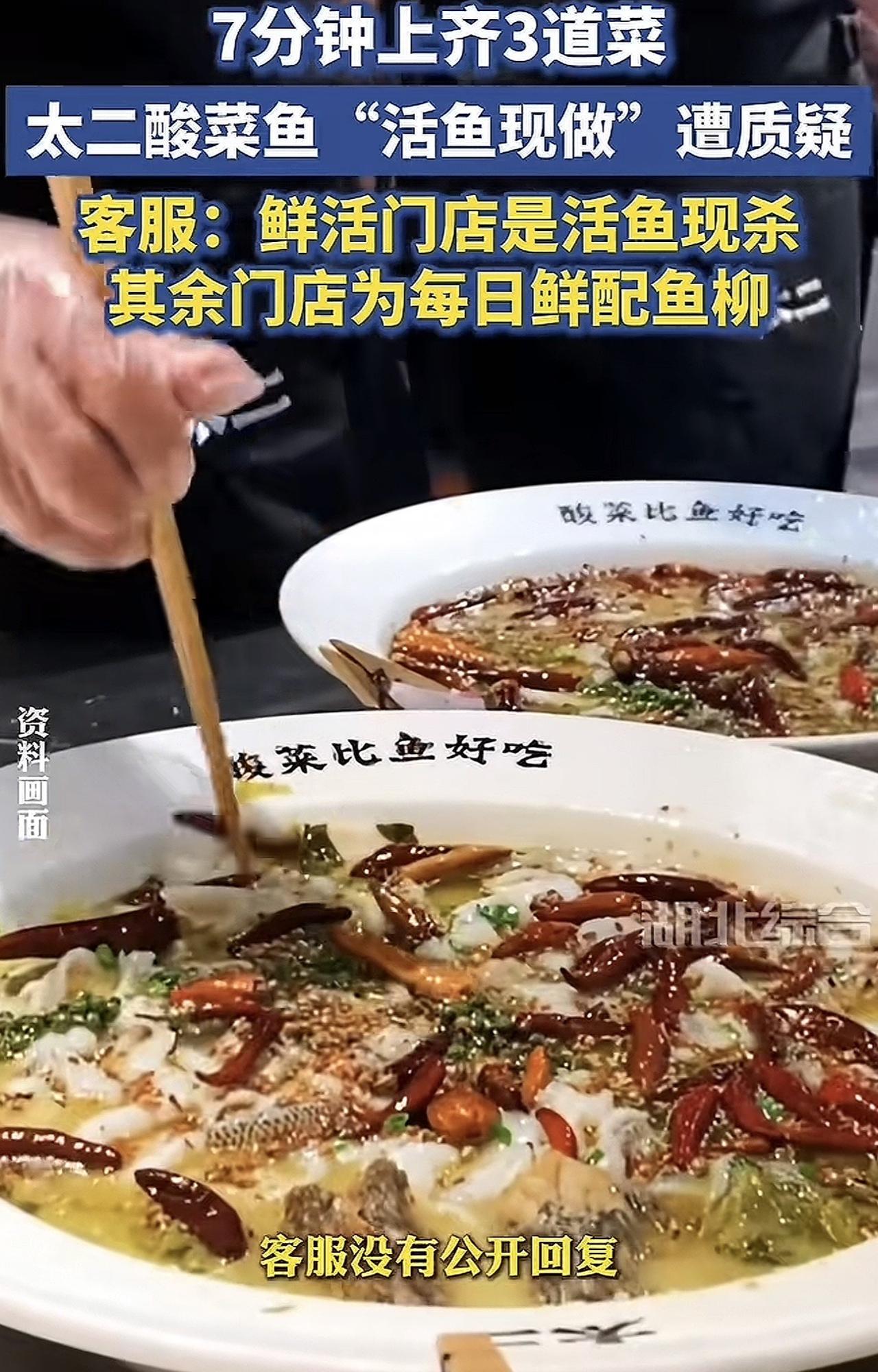如果要评选出一种中国人老少皆宜的美食,豆腐一定榜上有名,其原因不仅在于豆腐鲜嫩可口,更因为豆腐实在是千变万化,汪曾祺在《豆腐》一文中说了这奇妙。他说,点的老的是北豆腐,稍嫩的是南豆腐,再嫩的是豆腐脑,比豆腐脑更嫩的是水豆腐;豆腐压紧叫豆腐干,再薄点儿是豆腐片,更薄的是千张;把豆浆锅表面凝结的一层薄皮捞起来晾干,是油皮。梁实秋说他最喜欢的是香椿拌豆腐,朱自清在《冬天》里这么写,一“小洋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全家都眼巴巴地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 所以这个和蔼的父亲,愿意爬下站台去给他买橘子,也不新奇。我经常会想,孩子长大后,对家庭对故乡的记忆,似乎都是跟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而我这个几乎没给念念做个饭的妈妈,她是不是回忆不出什么来。 旅游也是,总是离不开尝尝当地特色。前一天在元阳,酒店餐有稻花鱼,顾名思义,在稻田里长大。司机师傅说,那个鱼不好吃,一股浓浓的泥土味,我带你们出去吃。虽然想试试看,但也不好拂了师傅的好意,就没吃。但是建水豆腐嘛,是一定要尝尝的。 建水豆腐比较特别,点卤之后用纱布包成块状,晾晒发酵成白豆腐。在古城里,处处可见豆腐摊,三三两两的食客围坐,发酵的豆腐块,在炭火的炙烤下,慢慢鼓起,就像蛋糕在烤箱里慢慢饱满起来一样很可爱,夹上一个从中间戳破,让热气散出,蘸不蘸佐料都各有各的好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老板一边给你烤豆腐,当你每吃一块时,一边投一粒黄豆到他旁边的碗里记账,古朴而不失趣味。 除了豆腐,我们还尝了草芽米线,草芽是生长在水底的植物,口感清甜,我开始还以为这里的葱味道这么好,原来这就是草芽,虽然米线中放的不多,但足以让小罐里增添了一抹绿色和清新。 如同这美丽的古城。
不放盐”三个字,能瞬间试出一家店是不是在用预制菜。点一份麻婆豆腐,跟服务员说:
【204评论】【51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