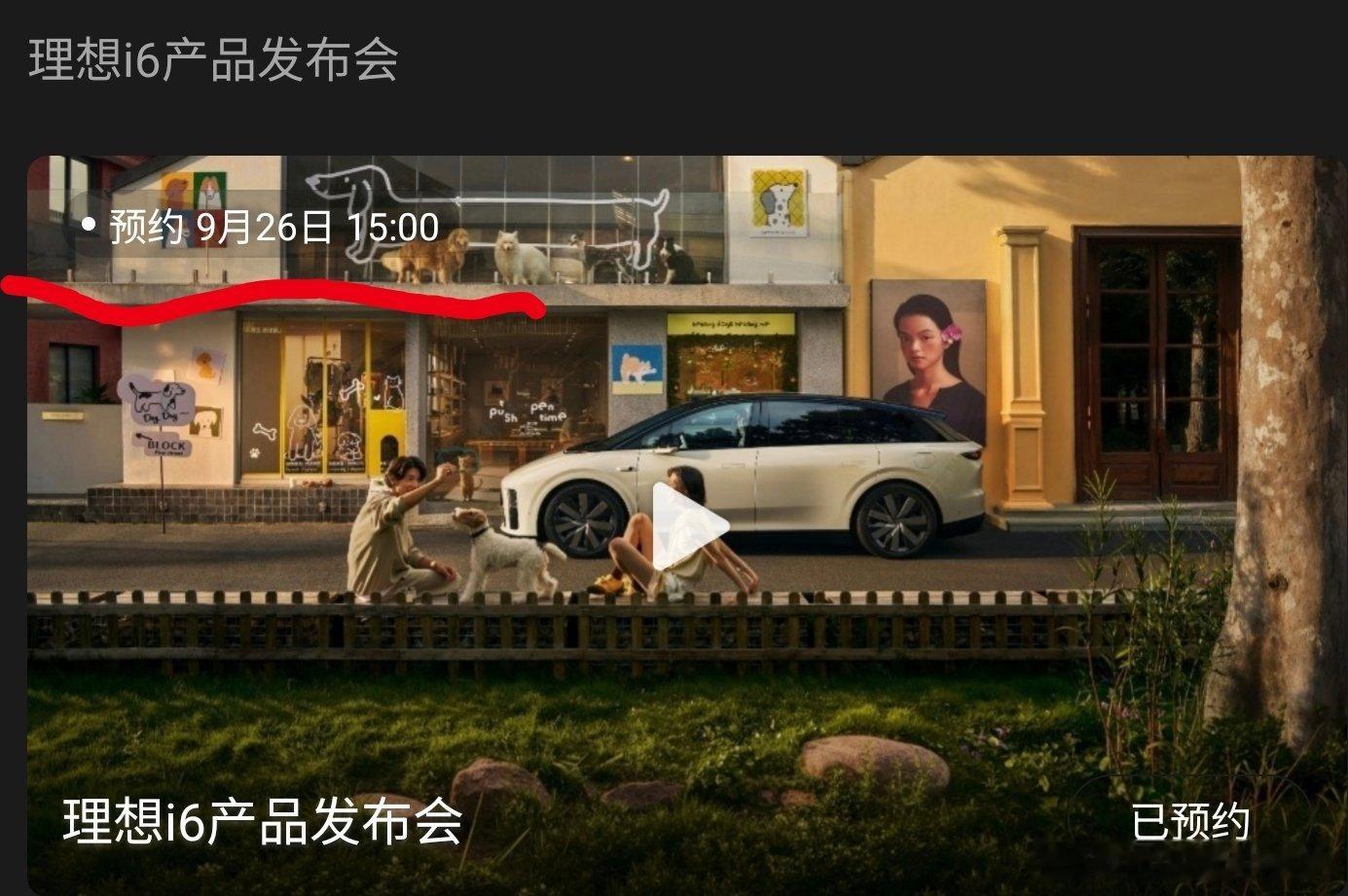□赵雅静
老屋南房的木梁垂着几缕蜘蛛网,在午后的阳光里轻轻晃荡,像是谁遗落在时光里的银丝。我搬开角落那个累积了半指厚灰的木箱,樟木的香气混着陈旧的布料气息弥漫开来——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终于完整地显露在我眼前。
银色的机头泛着温润的金属光泽,像是把三十多年的月光都揉碎了收在里面;黑色的台面边缘磨出了浅褐色的木纹,深浅交错,像母亲掌心的纹路;踏板下方的皮带松垮地垂着,但仍能看出当年紧绷时的弧度。我伸出手,指尖刚触到冰凉的机身,耳畔好似响起了熟悉的“咔嗒”声,一下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还记得儿时的冬天来得早,窗外的雪下得正紧,屋内却因这台缝纫机暖得发烫。
母亲脚踩着踏板,节奏均匀,不慌不忙。机针在灯光下上下翻飞,棉线在深色的灯芯绒上织出细密的纹路,像春蚕吐丝般,把寒冷都挡在了布料之外。
我趴在旁边的小板凳上,下巴搁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母亲的手。她的指尖缠着白色的纱布,是前一天给我缝棉袄扣子时被针扎破的。此刻,她握着布料的动作依然稳当,拇指轻轻推着布边,仿佛那根细小的钢针也听她的话,每一针都落得精准,每一线都走得匀称。
“慢些踩,线才能走得匀。”母亲见我看得入神,轻声说道,手里的活儿却没停。转眼工夫,一块平平无奇的白布,就变成了带着蕾丝花边的袖口,针脚细密的像天上的星星,找不到一点毛糙的痕迹。这台“蝴蝶牌”缝纫机是母亲当年最体面的嫁妆。外婆用了半年的积蓄,托人从上海捎来的。
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这台缝纫机不仅是摆设,更是母亲撑起一个家的底气——全家人的棉衣、我的书包、父亲的补丁裤子,都是它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每年秋天,母亲都会把旧衣拆了,浆洗干净,再按照我们的身量重新裁剪,用缝纫机拼织成新的外套。那些拼接的布料,颜色或许不那么统一,却总带着阳光和肥皂的清香。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要开运动会,吵着要一件红色的运动服。母亲翻遍了衣柜,只找到几块零碎的红布,最大的一块也不过巴掌大。她坐在缝纫机前,盯着布料看了半晌,眉头微蹙,忽然眼睛一亮,像是想到了好主意。
那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半梦半醒间,总能听到缝纫机的“咔嗒”声。第二天清晨,我一睁眼就看见床头摆着一件红色的运动服。领口用白色的布条镶了边,刚好遮住布料的接缝;袖口处缝着小小的五角星,用黄色的线绣了边,格外显眼;衣服的下摆还巧妙地拼了块格子布,既遮了补丁,又添了几分俏皮。虽然布料拼接的痕迹清晰可见,针脚也不如商店里的衣服整齐,却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衣服。
运动会那天,我穿着它跑八百米。风从领口灌进来,却一点也不冷,只觉得浑身都裹着母亲的体温。跑过终点线时,我听见同学们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心里比得了第一名还甜。
那件衣服我穿了三年,直到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仍舍不得扔,母亲便把它改成了书包,陪我走过了整个小学时光。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商场里的衣服挂满了货架,花色比母亲织的还要鲜艳,款式也更时髦。缝纫机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被母亲从堂屋挪到了南房的角落,慢慢蒙了一层薄灰。
我劝母亲把它卖掉,“现在谁还自己做衣服啊,占着地方不说,也值不了几个钱。”母亲却蹲下身,用软布蘸了温水,仔细擦拭着机头,从银色的旋钮到黑色的台面,连缝隙里的灰尘都不放过。“这机子还能用呢,你看这针脚,还是这么均匀。”说着,她找来电源插头接上,轻轻踩了踩踏板,机针依然能灵活地上下跳动,只是声音比从前沉了些,像老人咳嗽时带着的温和颤音。
母亲慢慢老了,膝盖不能长时间弯曲,头发也添了许多白霜,却偶尔还会用这台缝纫机缝补些东西——我儿子不小心刮破的牛仔裤,她会在破洞处缝朵小雏菊;邻居家孩子穿小的外套,她会改改袖口和下摆,让衣服重新合身。每次缝完,她都会把线轴一个个摆得整整齐齐,再从衣柜顶上取下那块印着“上海制造”的蓝色防尘布,小心翼翼地盖在机头上,抚平每一道褶皱,仿佛在珍藏一件稀世的宝贝。
这次整理老屋,我意外发现防尘布下面压着一沓泛黄的纸。纸张边缘已经发脆,展开来看,竟是母亲手绘的童装图纸。每张纸上都用铅笔标得清清楚楚:领口的弧度用圆规画得一丝不苟,袖口的尺寸旁写着“静静三岁,袖长18厘米”“静静五岁,袖长22厘米”,旁边还画着小小的梅花图案,花瓣的纹路细细密密,和当年她给我绣在裤子上的一模一样。
图纸的最后一页,是母亲用铅笔写的字,字迹有些颤抖,却一笔一画都很认真:“等静静长大了,给她缝件嫁衣。”原来她曾想过,用这台陪了她半生的缝纫机,为我缝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衣服,把所有的牵挂和疼爱,都缝进针脚里。
我的眼泪突然落了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了淡淡的墨迹。那不是普通的墨迹,是岁月的痕迹,是母亲未曾说出口的爱。这台缝纫机,早已不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它是母亲的时光容器,把三十多年的爱与牵挂,一针一线地缝进了岁月里,缝进了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
我把缝纫机搬到了自己的家里,放在阳台的窗边。周末的午后,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坐在缝纫机前,踩起了踏板。
一开始,机针总是断,棉线在布料上绕成乱麻,手指也被针扎出了好几个小红点,疼得我直咧嘴。可每当听到“咔嗒”声响起,就像母亲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声说“慢些,别急”。
我慢慢找到节奏,看着机针在布料上穿梭,看着棉线织出细密的纹路,忽然就懂了母亲当年的心境——那不是简单的缝补,是把心意揉进针脚里,把温暖织进岁月里。
这台蝴蝶牌缝纫机,不是一台普通的机器。它是母亲的青春,更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无声的对话。
阳光落在机头上,泛着柔和的光,像在诉说着那些被棉线串联起来的日子。那些藏在针脚里的时光,那些浸在“咔嗒”声里的爱,会像年轮一样,永远刻在我的生命里。
![西贝的营销真他娘的是个天才[doge][doge][doge]~七岁的毛毛哭着闹](http://image.uczzd.cn/1043082693323147044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