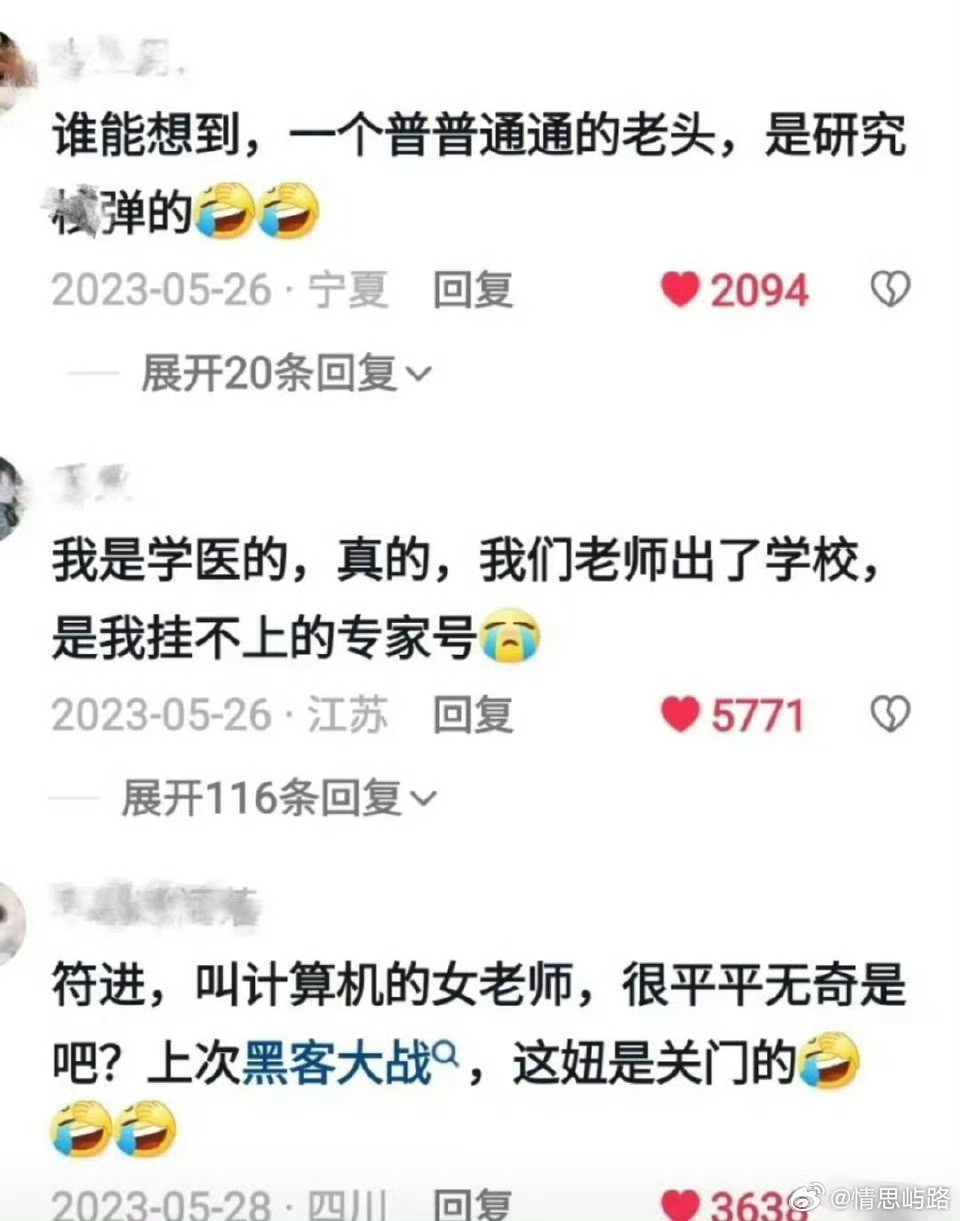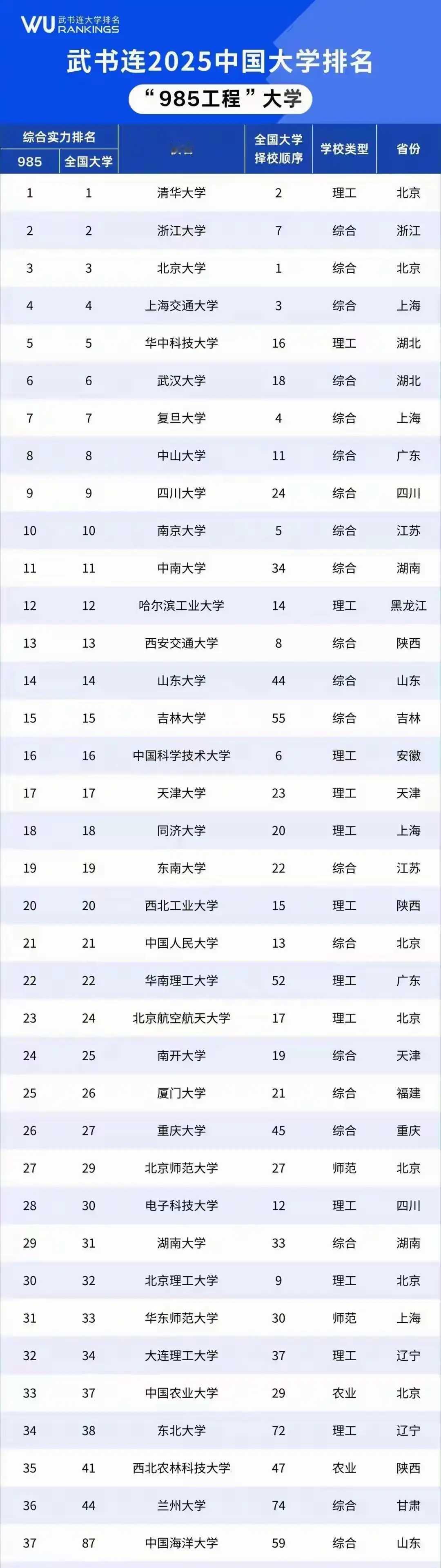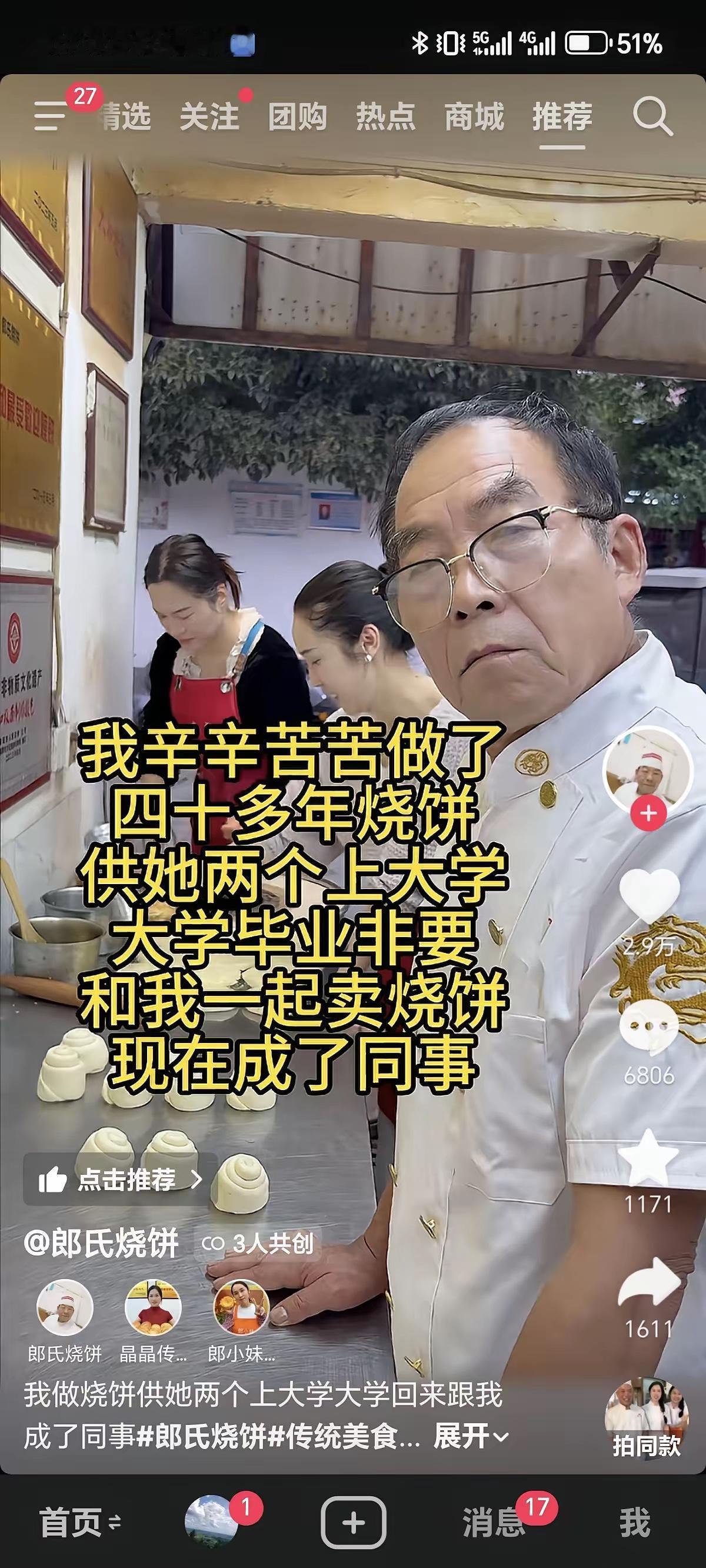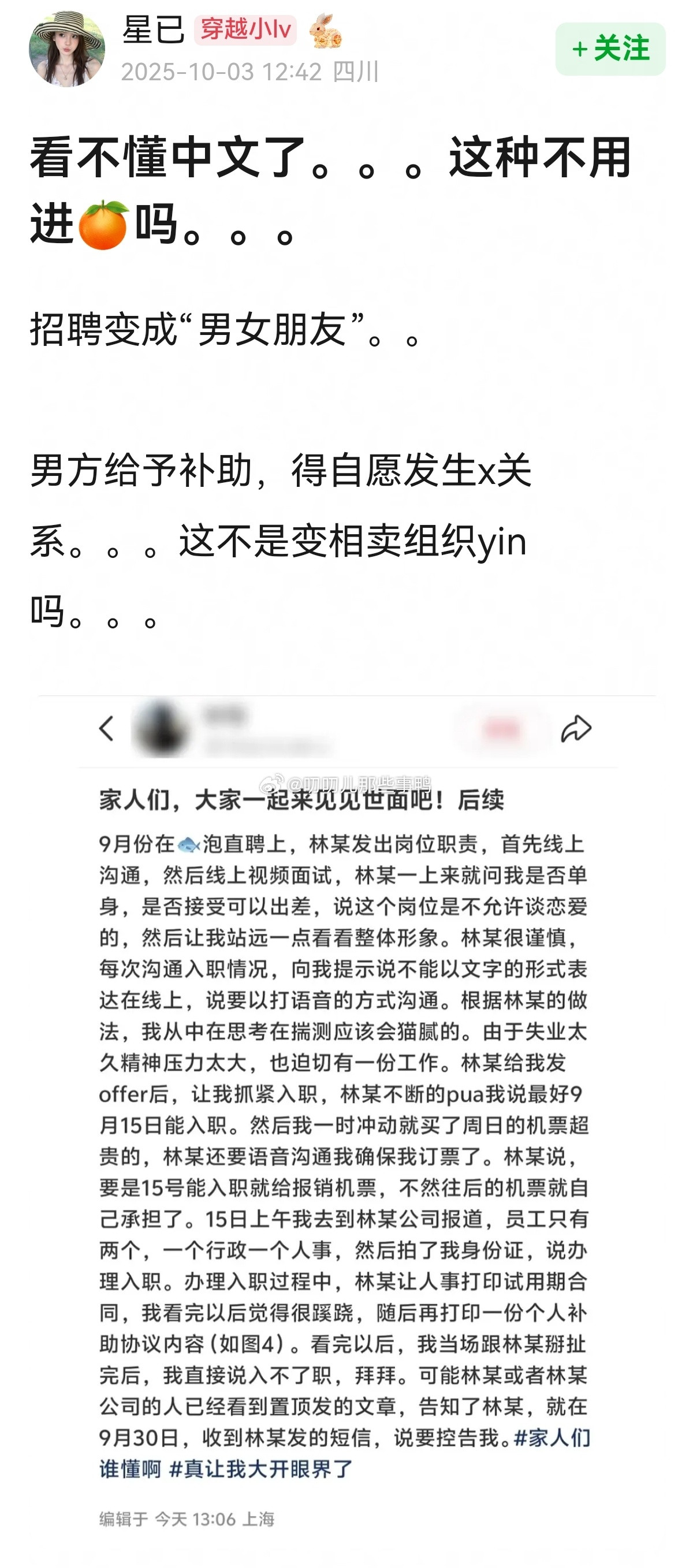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王德峰前几天说的一句话,把全网都震住了:“我堂堂复旦教授,我的儿子从小念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到头来却只考上了二本!” 话音刚落,台下一片哗然。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德峰看着台下震惊的表情,接着说了四个字:“这就是命!” 这话从一个哲学教授嘴里说出来,简直就是学术界的地震。 要知道,王德峰可不是什么佛系教授。这个从23岁电工逆袭到复旦哲学院副院长的男人,一直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1978年,还在做电工的王德峰听说高考恢复了,立马扔下手中的工具:“我不信命运,我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三年苦读,一朝成功。从工厂到复旦,从工人到教授,王德峰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努力真的能改变命运。 所以当儿子出生那天,王德峰就下定决心:“我儿子一定要比我更厉害!” 他给儿子制定了完美的人生规划: 3岁上最贵的早教班,老师都是海归博士。 小学进上海最好的私立学校,每年学费20万。 那些年的王德峰,下班后从不会像其他同事那样约着喝茶聊天,总是揣着刚打印好的名校资料往家赶,心里盘算着怎么把儿子的每一步都嵌进“最优解”里。他总觉得自己能从电工拼到复旦,靠的就是精准规划和死磕到底,儿子握着更好的“牌”,没理由走得比自己差。 初中时他托了三层关系,把儿子送进了上海那所挤破头的重点中学,光是给老师的拜访礼就挑了半个月,就怕孩子在起跑线上差了半分。每天晚上不管学院的事多忙,他都会坐在儿子书桌旁陪着刷题,遇到儿子解不出的数学题,他会把哲学理论暂且搁在一边,拿着草稿纸一步步推导,直到孩子点头说懂了才肯休息。 他甚至提前五年就研究好了上海各所高中的升学率,把儿子的目标锁定在那所常年出清北学子的顶尖高中,为了让儿子达到自主招生的标准,周末报了四个培优班,奥数、英语、物理轮番上阵,儿子偶尔说一句“爸,我有点累”,他都会语重心长地说:“爸爸当年在工厂里啃书本,比这苦十倍,现在不拼,将来怎么站得高?” 可命运好像开了个玩笑,儿子高中三年明明坐在教室里最前排,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每次模考却总在中游徘徊。王德峰急得睡不着觉,托朋友找了市重点的特级教师来家里补课,每小时费用抵得上普通工人半个月工资,可儿子的成绩就像被钉住了似的,始终没冲上去。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王德峰正在给学生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手机屏幕一亮跳出儿子的消息,那串数字让他握着粉笔的手顿了足足三秒,粉笔灰簌簌落在讲台上。他强撑着讲完最后十分钟,走出教室就蹲在走廊尽头,看着楼下往来的学生,突然想起自己当年拿着复旦录取通知书时,在工厂宿舍里激动得一夜没睡的样子。 后来他在讲座上说出那句“这就是命”时,台下有人觉得是教授在凡尔赛,有人觉得是努力过后的无奈,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出这四个字前,他纠结了多久。他这辈子都在跟命运较劲,靠努力把自己的人生轨迹掰向了光明的方向,却偏偏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努力未必全能如愿”的真相。 有次他去儿子的二本学校看他,发现孩子在宿舍里养了几盆多肉,还跟着社团一起做公益活动,说起专业课上的有趣发现时,眼睛亮得像藏了星星。那天儿子拉着他去食堂吃饭,给他打了一份糖醋排骨,笑着说:“爸,这里的排骨比家里的好吃,你尝尝。”看着儿子轻松的样子,王德峰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总想着让儿子“更厉害”,却忘了问孩子真正想要什么。 他想起自己23岁当电工时,每天下班抱着书本啃,不是因为有人逼,而是打心底里想通过学习改变生活。可儿子从三岁起就被塞进各种培训班,沿着他规划的路线往前走,那些“最好的学校”“最贵的课程”,未必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更像是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强行套在了儿子身上。 现在再有人问他怎么看待“命”,他不会再像年轻时那样一口否定,也不会单纯归因于运气。他会说,努力当然重要,就像他自己,如果当年没抓住高考的机会,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可也得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节奏,就像有的花春天开,有的花秋天开,不能因为期待春天的花,就逼着秋天的花提前绽放。 王德峰说“这就是命”,其实不是向命运低头,而是经历过期待与落差后,对人生有了更通透的理解。他依然相信努力的意义,只是不再把“成功”定义为“必须考上名校”,而是看到了孩子健康快乐、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是一种圆满。 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觉得自己走过的弯路,孩子不能再走;自己没实现的梦想,要让孩子替自己实现。可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天赋和热爱,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就像王德峰的儿子,虽然没考上名校,却在自己的学校里过得充实快乐,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