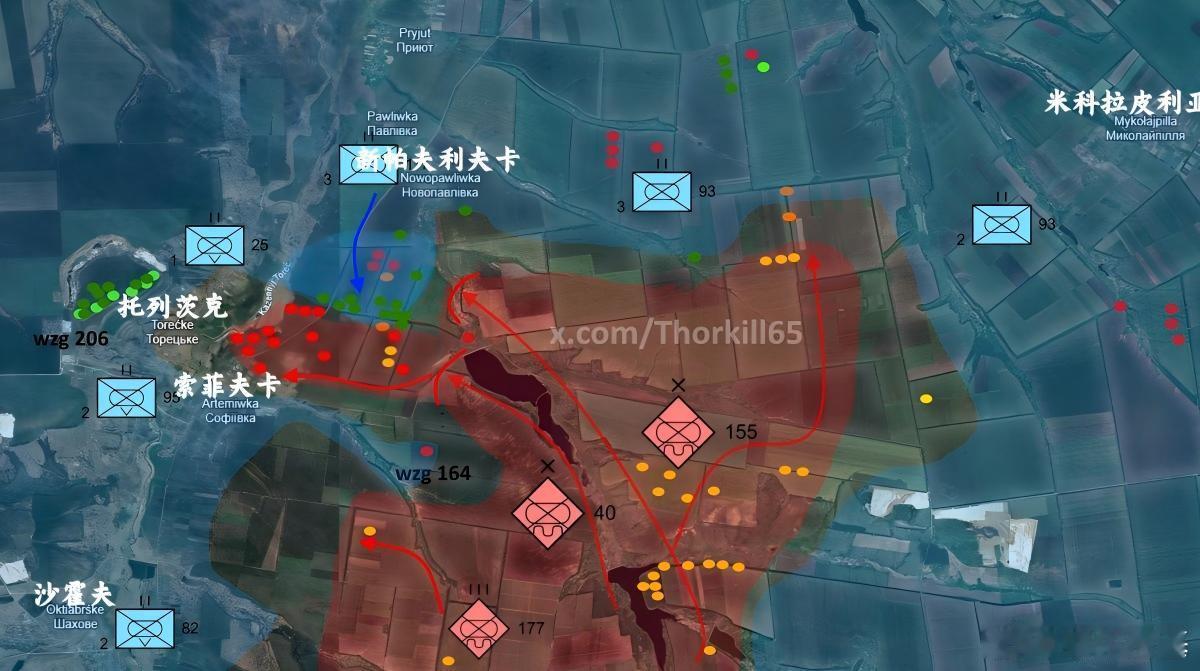谈谈我对于《红楼梦》索隐派等看法,我觉得,红楼梦本身并不是一部写宏大叙事的小说,之所以有现在的地位,主要是它揭露了“人性底色”,它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揭露了血淋淋的社会现实,但又包装上精美的爱情故事。若对书中各种社会现实选择性失明,只聚焦于“宝黛爱情”及风花雪月,无异于剔除了《红楼梦》的内核,将一部家族和社会末世血泪,阉割成闺阁的言情传奇。索隐派如刘心武将秦可卿附会为“废太子之女”,周汝昌给史湘云加戏,将个人情感凌驾于原著之上,本质上是对原作的“二次创作”,将红楼梦降格为甄嬛传之类的古装悬疑小说。
原著里秦可卿出身寒微,从养生堂抱来,脂批也未透露她有“公主”信息。刘心武的证据全部是影射、谐音、暗号,其实跟秦可卿没有半点关系。
原著中的秦可卿的作用,是因为她死于“情”和“淫”,是对于贾府的第一个警告,与后面贾府中的贾珍父子、贾赦、贾琏及薛蟠等人相呼应,这就是秦可卿对于本书的最大的价值,把个人的悲剧与整个家族的悲剧、危机结合起来,具备现实意义。刘心武却把秦的悲剧性全部抹去,换成了宫廷政变,原本的警示作用全无,成为政治野史,瞬间降低了全书的格调。
周汝昌的“湘云中心论”,黛玉靠边站,完全是他个人的喜好。他把脂砚斋认定是史湘云原型。湘云瞬间从宝玉的妹妹,一跃成为“精神伴侣”,成为大观园的“大女主”
这样一解释,黛玉早逝、宝钗守寡的悲剧结局,瞬间失去了原有的悲剧色彩,全部为宝玉和湘云的“美满婚姻”作铺垫。原作的悲剧色彩全无,家族悲剧、女性悲剧的思想性被周汝昌扔到荒郊野外。
刘心武、周汝昌等所谓红学家的套路一致,选书中的边角料放大,然后反推作者本意。先设定秦可卿是公主、湘云成大女主,然后去书中寻找蛛丝马迹,然后牵强附会。本质上是二次创作,完全不遵重原作者本意。刘心武版红楼梦变成了《大清政治野史-公主潜伏》的悬疑小说,满足了公众的猎奇心理,但原作的思想性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周汝昌版红楼梦变成了《金玉良缘现实版-宝玉终于娶对了人》,满足了个人的喜好,完全无视原著的核心内涵,降级成为另类版甄嬛传,现实主义巨著变成香艳版群女争夫。
他们不关心曹雪芹到底在悲悯什么,不去研究原作者的本意,而是借红楼之瓶,强行装自己的酒。公众爱听宫廷内斗、九子夺嫡,爱听“错位版CP”,他们就喂给公众。满足了猎奇、狗血趣味,卖自己的书、出自己的名。
红楼梦之所以有现在的地位,在于它的思想性、文学性,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是“宝黛爱情”明线后的一条暗线。无论是对于贾雨村乱判葫芦案、香菱被二次贩卖、王熙凤和老尼姑害死一对恋人,还是书中众多女性的悲剧命运,都在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家族烂到底的现实。曹雪芹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家族内男性群体的淫乱、目无王法,其实是对于家族倾覆的反思与批判。
刘心武、周汝昌等人完全不顾原作所表达的思想,硬把红楼梦二次创作成了一个普通悬疑小说,成为迎合众人的爽文。把“人性百科全书”写成了“谁才是隐藏的大女主”,其实和网络普通写手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