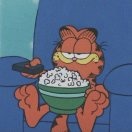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那个宽厚的肩膀微微耸动着,像是在压抑着什么。就在他侧身拐过楼梯转角时,我看见了这个五十二岁农村汉子眼里闪烁的泪光。那一刻,九月的青岛突然变得模糊不清。 这是2000年的初秋。三天前,那张姗姗来迟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送到了我们那个鲁西南的小村庄。父亲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反复摩挲着通知书光滑的纸面,嘴里喃喃着:“来了,总算来了。”那时的我,还沉浸在即将远行的兴奋中,全然没有注意到父亲眼神里除了喜悦,还有别的什么。 雨是从清晨开始下的。父亲推着那辆老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让我坐在后座上。“抓紧了。”他说。然后我们便一头扎进九月的雨幕里。泥泞的土路在雨中变得格外难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脚踏板,车轮不时陷进泥坑里。我坐在后面,能清楚地看见雨水顺着他的脖颈流进衣领,能听见他略显粗重的喘息声。 我们要去县城办理粮油关系和户口迁移。在那个世纪之交的年份,这些纸质证明依然是一个农村孩子走进城市的通行证。 乡政府的办事员慢条斯理地翻看着材料,父亲站在柜台前,微微弓着腰,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容。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这个在我心中永远挺拔如山的男人,原来也有这样谦卑的姿态。他一遍遍地解释着:“孩子考上大学了,要去青岛。”仿佛这不是解释,而是一种难掩的骄傲。 所有手续办完,已是下午三点。雨还在下,父亲把那些盖着红印章的证明用塑料布层层包好,塞进内衣口袋,然后拍了拍胸口:“这可不能湿了。” 回家的路上,雨更大了。父亲蹬车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后背已经完全湿透,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我要求下来走路,他却不允:“坐好,马上就到家了。”那一刻,我看着这个在雨中奋力蹬车的背影,突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手续的办理,更是一个父亲在用他的方式,为我铺就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第二天,我们踏上了去青岛的火车。从未出过远门的我们在济宁火车站错过了原定的列车。父亲急得满头大汗,背着那个塞满被褥和衣服的巨大行囊,在站台上不知所措地转着圈。那行囊是如此之大,压得他的身子微微前倾,走起路来踉踉跄跄。 好在,这个世界的善意总在关键时刻显现。一位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安排我们上了一列快车:“到济南换车,来得及。”父亲千恩万谢,那神情,像是遇到了救星。 在济南站,父亲背着行囊,一边张望一边小跑,宽大的行囊在他肩头左右摇晃,他的脚步也跟着不时踉跄。我紧跟在他身后,看着这个略显笨拙的背影在拥挤的人流中艰难穿行,突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以前在课本上读到时并无太多感触,此刻却觉得每一个字都砸在心上。 终于到了青岛。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所在的城市。父亲深吸一口气:“这空气,不一样。” 报到日的校园人声鼎沸。父亲依旧背着那个巨大的行囊,按照行程单上的指示,带着我奔波于各个报到点。他坚持要亲自办理每一个手续,在每一个队伍后排队。填表时,他戴上老花镜,一笔一画写得极其认真,仿佛要把所有的嘱托都写进那些表格里。 领到被褥和生活用品后,我们来到宿舍。父亲执意要为我铺床,他站在上铺,笨拙而又仔细地整理着床单被角。午后四点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我才突然发现,父亲真的老了。 一切安排妥当,已是下午四点多。父亲必须赶当晚的火车回去——多住一晚就要多花一晚的钱。他站在宿舍中央,搓着手,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父亲本就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此刻更是语塞。最后,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照顾好自己。” 然后,他转身离去。 就在那个转身的瞬间,我看见了他眼里的泪光。这个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村汉子,这个在我心中坚不可摧的男人,此刻却红了眼眶。那闪烁的泪珠里,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牵挂,或许还有太多的不放心——他的儿子,第一次要独自生活在四百公里外的陌生城市了。 我站在宿舍门口,久久没有动弹。父亲离去的背影定格在2000年9月的那个黄昏,定格在我十八岁的记忆里。那个背着行囊在雨中骑车的背影,那个在火车站踉跄奔跑的背影,那个红着眼眶转身离去的背影,共同构成了我大学时代最深刻的印记。 多年后,当我也有了需要送别的孩子,我才真正明白父亲当年的眼泪。那是一个父亲最深沉的表达——他亲手把你推向更广阔的世界,却又在转身的瞬间,让所有的不舍化作无声的泪。 窗外的青岛华灯初上,海风依旧。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真正开始了独立的人生。而父亲转身时的那滴泪,将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提醒着我:无论走多远,都有一个男人在他乡,用他最朴素的方式,深深地爱着我。 那滴泪,是告别,更是祝福。是一个农村父亲能给儿子的最珍贵的行囊。
我站在宿舍门口,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那个宽厚的肩膀微微耸动着,像是在压抑着什
紫槐
2025-10-07 18:20:01
0
阅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