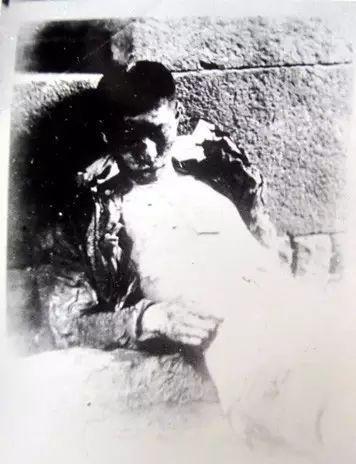清末的刺客都有多拼命?当年同盟会内部曾经专门设有一个暗杀部门,19岁的福建侯官人方君瑛为部长,主要成员有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等年轻人。 1905年秋,东京的空气混着墨香与火药味。留日的中国学生在一间旧茶馆里秘密聚会,门窗紧闭,灯火昏黄。他们的谈话里满是“革命”“推翻满清”“流血”这些字眼。茶桌上放着一本新印的《民报》,扉页上印着一句话——“革命,非流血不能成”。 这一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在演讲中说,光靠舌头喊口号没用,必须有行动。年轻人点头,他们的血气正旺,理想刚燃。革命,成了他们唯一的信仰。 可理想要靠命去换。自1895年乙未失败以来,一次次起义、一轮轮清洗,让无数年轻人明白,清政府靠的是枪,不是讲理。于是,暗杀这种最直接、最危险、最震撼的方式,成了他们的选择。 在东京,同盟会的“实行部”被秘密成立。名义上是负责行动,实际上就是专搞暗杀。十九岁的方君瑛——一个福建侯官出身的姑娘,被推举为负责人。她留着短发,穿男装,说话干脆。没人觉得她像个女人,倒更像个军官。 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一串名字,从此和炸药、刺刀绑在一起。那群人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却在密室里反复研究手雷结构、炸药配比、引线延时。他们的理想,不在书桌上,而在火药桶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暗杀不是犯罪,而是信仰的另一种形态。 方君瑛生于1884年,家族满门忠烈。她的弟弟方声洞,后来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兄妹二人,一个在战场,一个在暗处。方家是典型的革命之家——全家以死为志,不以退为荣。 她早年留学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清廷腐败、列强横行,她看在眼里。她的朋友说,方君瑛的笔记本里写满“救国”“复汉”的字样,还夹着一张炸弹结构草图。 她在同盟会中负责“实行部”,统筹暗杀行动。这不是虚职,她要掌握人员分配、武器制造、经费筹措。吴玉章负责联系国外买药原料,喻培伦和黎仲实在东京郊区实验炸弹。炸一次,失败一次,再换配方,再试。几次爆炸差点炸塌了仓库,他们就换地方继续。 他们白天穿长袍、读书,晚上聚在狭小房间,研究如何安放炸弹、如何引爆列车、如何制成袖珍雷管。方君瑛在一旁记录,声音冷静。她知道,这些炸药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国人”。 她说过一句话,被后来人传为口号——“用一命换百命,天下自有明天。”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她每天面对的现实。那些年轻人活在暗杀名单的背面,每个人都知道,行动失败,就是死亡。 “实行部”的第一个目标是清廷重臣——摄政王载沣。那是权力的核心人物,刺杀他,意味着向帝国宣战。任务由黄复生、喻培伦执行,他们带着炸药潜入北京,在宫门附近布点。 那晚,他们等了三个小时。风吹过煤气灯,炸药埋在车道下。可引线受潮,未能点燃。两人被捕。黄复生在狱中咬断舌头,喻培伦自尽。 东京的同盟会收到消息,方君瑛没有哭。她在笔记上写了四个字:“行动继续。” 暗杀,不只是行动,更是一种精神传染。那几年,从东京到广州,从香港到汉口,同盟会的青年一批批涌向死亡。 吴玉章回忆,那些年几乎每天都有人写遗书。有人用毛笔写“革命不成,毋复相见”;有人在炸弹壳上刻字:“此弹为民请命。”他们都笑着出发,从不返回。 黎仲实负责掩护,曾醒专门跑情报。他们的通信用的是火柴盒暗语,遇到查验就烧掉。每一次寄信,都像赌博。有人刚写完密码信,就在码头被捕,再没回来。 暗杀行动接连失败,很多年轻人死在未爆的炸药边。有人炸死自己,有人被绞刑,有人被清军枪决。可同盟会的通缉名单反而越长。政府越严,行动越多。 1910年之后,清政府在全国布控,凡是携炸药、买硫磺的学生都被严查。同盟会的地下点被迫转入香港、南洋。方君瑛负责疏散幸存者。她的头发在短短几年间白了半边。 那时她不过二十多岁,却像老去了半生。 行动一再失败,她没有退。她开始负责筹款——从福建、香港的商会筹集军费,从海外留学生募集炸药。有人劝她离开,说女人何苦做这种事。她只是摇头,把钱塞进炸药箱。 那几年,同盟会的暗杀成了世界新闻。日本警察写报告说:“中国革命党人,年少激进,不畏死。”这不是赞美,是震惊。 当时的中国,贫弱而腐败。有人求洋务,有人修宪,而这些年轻人选择了最直接的办法——流血。 他们没能杀死摄政王,也没能炸毁帝国的根基。可他们用自己的命,在那个麻木的时代,炸响了一声警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坍塌。那些曾经潜伏在暗处的刺客,终于迎来了黎明。 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东京,幸存的同盟会员夜里痛哭。有人举杯纪念死者,有人默默写下名字——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方声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