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国第一性学家”李银河含泪将亡夫王小波的遗体,送去火化,不料工作人员按了几下焚化炉开关,机器都没反应。后来他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这位先生,还请你帮个忙,你的东西我处理不了。 2024年李银河的书桌上,摆着个旧铁皮盒,里面是王小波的钢笔。钢笔杆上有牙印,是他写稿时下意识咬出来的。盒底压着张便签,是1997年4月10日的字迹:“给银河带话梅。” 李银河拿起钢笔,笔尖还能渗出淡蓝墨水,像他没说完的话。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和三十年前他们院子里的一样。 1997年4月11日,李银河从外地赶回家时,门锁没换。钥匙插进去转两圈,门“吱呀”一声开了,像往常一样。客厅的灯还亮着,王小波常坐的藤椅上搭着他的毛衣。 书桌上摊着《黑铁时代》手稿,最后一页画着个笑脸。她走过去摸手稿,纸还带着点余温,像他刚离开。殡仪馆的人来抬遗体时,李银河在他口袋里摸到个小纸包。打开是话梅糖,还是她爱吃的甘草味,包装纸皱巴巴的。 “他昨天还说,等你回来一起吃。”邻居阿姨红着眼说。 去火化场的路上,李银河把糖揣在兜里,手指反复摩挲包装纸。车窗外的树飞快后退,她突然想起他们第一次约会,他也是这样揣着糖。 火化炉启动时,李银河站在玻璃外,看着遗体慢慢移动进去。刚听到“轰隆”声,机器突然停了,指示灯变成红色。工作人员急得拍机器:“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 李银河反而平静下来,对着玻璃轻声说:“你是不是还没放心?”话音刚落,机器突然“咔嗒”响了声,指示灯又变绿了,后来工作人员说,是线路接触不良。 王小波生前,《黄金时代》被退稿时,他们常坐在院子里聊天。他拿着退稿信笑:“他们说我写得‘出格’,其实是怕真话。”李银河给他剥橘子:“没关系,我们自己印了给朋友看。” 有次他熬夜改稿,李银河起来给他热牛奶,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手稿上落着片玉兰花瓣,是从窗外飘进来的,他没舍得拂掉。 1998年《黄金时代》终于出版,首印五千册很快卖完。李银河去书店签售,有人抱着书哭:“王老师的书,我等了五年。”她给每个读者递上张便签,上面是王小波的一句话:“爱你就像爱生命。” 有个高中生说,读了这本书,他决定要勇敢做自己。李银河看着他,想起王小波常说的“年轻人要敢想敢说”。 2003年,李银河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个纸箱,里面全是读者来信。有的信写得很长,说《黄金时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有个监狱里的犯人写信,说读了书后想重新做人。 李银河把信都整理好,放在铁皮盒旁边,像给他留着。她想,这些信,他要是能看到,肯定会很开心。 2024年的春天,李银河还在整理王小波的手稿。有篇未完成的短篇,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结尾处写着:“银河笑起来,像玉兰花一样。” 她拿起钢笔,在后面补了句:“我也是。”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手稿上,字迹慢慢干了,像他应了声。 如今,李银河还住在老房子里,院子里种着玉兰树。每年花开时,她会摘几朵放在王小波的照片前。书桌上的铁皮盒总开着,钢笔就放在旁边,随时能写。 《黄金时代》已经再版二十多次,每次再版,她都会写篇序言。序言里总会提到那个铁皮盒,提到那支钢笔,提到他没说完的话。 有人问李银河,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放下。她笑着指了指书桌上的书:“他没走,就在这些字里。”风从窗外吹进来,翻开《黄金时代》的某一页,停在“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李银河拿起书,轻声念了起来,声音很轻,却像能传到很远的地方。院子里的玉兰花,在风里轻轻摇晃,像在应和。 信源:李银河:我活着,王小波就活在我生命里.北京知青网.2012/06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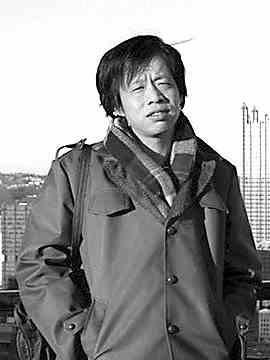









消逝的光影
出格吗...不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