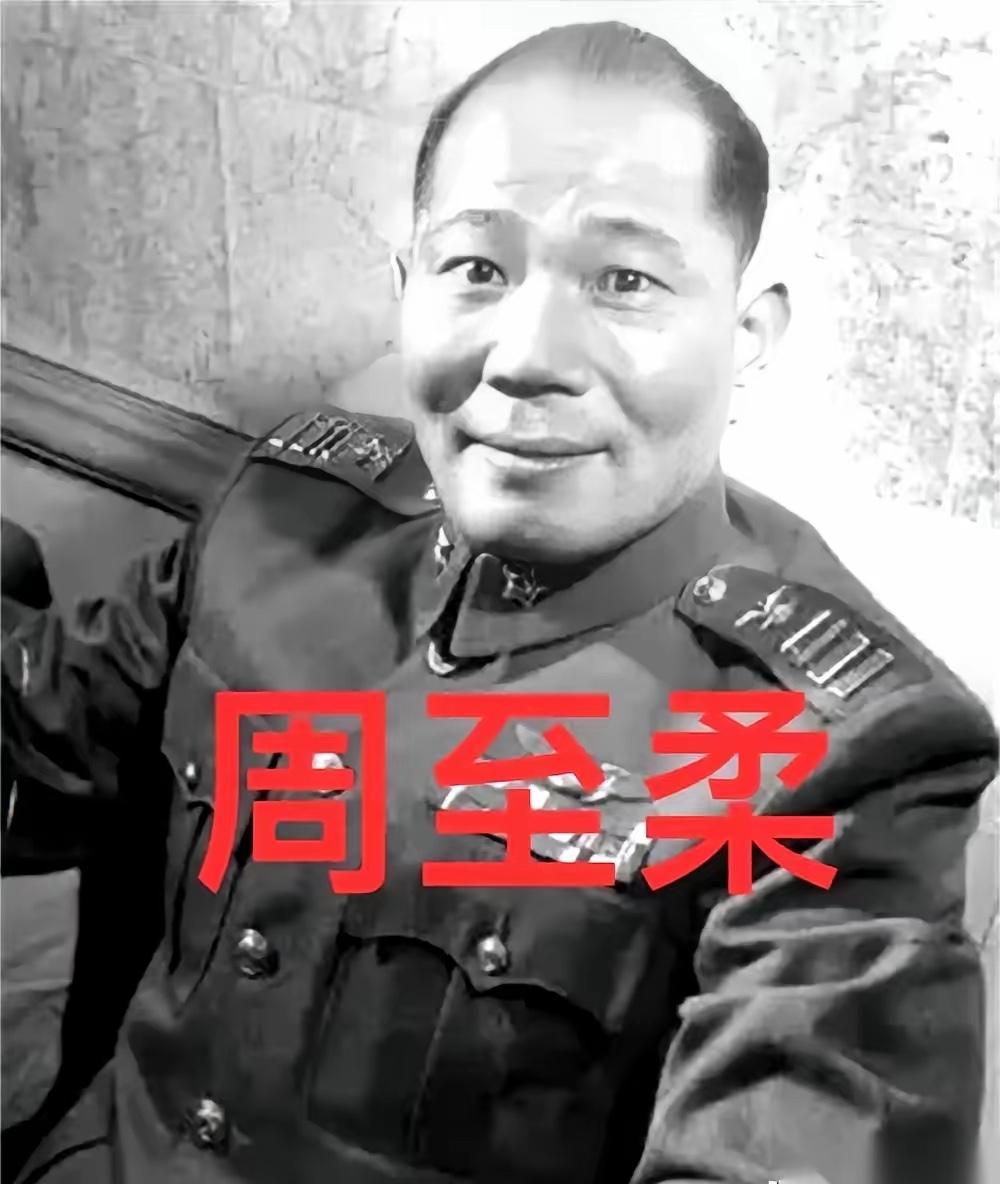毛主席给吴石将军题诗,这是很少见的,这是对隐蔽战线工作的认可。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生在福州,1894年。家里读书人出身,规矩管得紧。 上学时就有点“过目不忘”的意思,老师一边讲课他一边画地图,画完还能顺手补几个注释。后来保定军校毕业,成绩第一,又跑去日本陆军大学,还是第一。 人家说他是“十二能人”,那时候军队讲究得是打仗,他偏会画、会写、会翻英日文,骑马射击样样精,手还稳得很,拆枪能拆到零件全摆整齐。 这样的人,进了国民政府,不难混。他在军政体系里一路走,坐得住,也听得懂场面话。 但时间长了,看得东西多了,心里也开始拧巴了。 抗战结束以后,他回到南京,走在街上,瞧见原来打着“接收”名头的人在抢仓库,百姓围着看,一个老太太说,“又是来洗的”,他没吭声。 只是回去坐下,把军帽摘了,放在桌上,一动不动坐了半小时。 那段时间,他和一些旧朋友见得勤了。 其中有个叫何遂的,两人是早年打仗时结下的交情。 1947年春天,吴石找上门,说,“我想换条路走。”何遂懂他,也没多问,只领他去见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人。见面那天是在锦江饭店旁边的公寓楼里,房间不大,茶水都没续,一小时不到就谈完了。 出来时他脸上没表情,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局面就变了。 他还是那个国防部史料局的局长,表面看没什么不同,可桌上的文件他看得更仔细了。 别人翻过去的,他折个角;别人说“归档”的,他说“我再看看”。那时候国民党正忙着打内战,他负责的,是抗战史料的整理,但谁都知道,“整理”这个词,水有多深。 他身边慢慢绕起一张网,有几个老朋友变成了线头:吴仲禧、何康、胡宗宪。 仲禧是老同学,早就入了党;何康是何遂的儿子;胡宗宪是他带过的学生,做情报科科长。这仨人,一个在监察局,一个在交通线,一个在“剿总”。看上去互不相关,其实每隔十天半个月,就有一份材料从吴石的办公室绕一圈,穿过手提包、茶叶罐、旧书壳,出现在上海地下党那边的情报袋子里。 他不是那种心急的人,一次,吴仲禧要去徐州“剿总”走一趟,临行前吴石写了封信,让他带去交给李树正。 李是“剿总”参谋长,也是吴石的学生。 仲禧到了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还带他进了作战室。 屋里挂着大幅兵力部署图,他假装看不懂,李就在一旁讲解,他装傻点头,脑子飞快地记。 回上海后,他在旅馆一晚上画了五张图,把从商丘到海州的兵力位置画得一清二楚。这些图,后来在淮海战役前被送到前线。 1949年初,南京局势已经不稳了。 吴石跑得更勤,从上海带一批材料去南京,送完再回来接新任务。有一天,他从南京回来,穿着灰风衣,走进屋就说:“长江那头,要动了。” 第二天,他就开始安排起义的事情。 林遵的名字,这时候冒了出来。 那是第二舰队司令,也是福建人。原本想着保船保人,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吴石找到他,俩人坐在南京江边一个小茶馆,天已经擦黑,没点灯,桌子上只有一张折叠的纸。 吴石说,“这事,我劝不了你,但你要是动了这念头,我给你后路。”林遵没表态,只是低头点烟,火光一闪,眼睛有点红。 几天后,舰队起义。 吴石坐在办公室听电报,听完什么都没说,关掉收音机,把一张旧地图收进抽屉,动手把办公桌的抽屉全清空。 他知道,该走了。 到了1949年夏天,他接到调令,要调往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个身份高,是保护伞,也可能是靶子。有人问他:“你想清楚了吗?”他说:“去。”没再多说一句。 到台北后,他住在一个老式的眷村房里,屋子不大,门口种两盆兰花。 他穿着中山装上下班,和别人看起来没两样。白天开会,晚上画图。他身边有个联络员,叫朱枫。外表看是个普通太太,其实是地下党派过去的交通员。每次来访,她带着点水果,走时手里多一个旧皮包。没人注意。 有一次,他拿出一份台湾防御图,说:“这个,你带回去。” 她看了一眼,说:“这个量太大。”他顿了顿,说:“你要是带不回去,我再画一份。”朱枫没接话,把图收好,笑着说:“能带。” 事情就坏在1950年年初。台省工委的头被抓了,转天就投了。一整条地下网络被拦腰斩断。朱枫本来已经离台,在舟山被拦下来。接着,国防部特务来敲门,说吴石“有事要问”。他不慌,换了件干净的衬衣,把眼镜擦干净,出门前把书桌上的纸全撕了。 在看守所里,他被打了一只眼,走路一瘸一拐。 有人听见他咳嗽得厉害,一直没见医。每天都有人来问“你和谁联系”,他一句不讲。最后他提笔写了一封信,写给妻子,说:“门户看好,孩子别怕,家里有亲戚。”末尾附了一首小诗,没有愤怒,也没有哭诉,只有四句话,说得平静。 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枪响那天,有风。 太阳往下走了一点,影子拉得长。他走在队伍最前面,没戴帽,脸干净,步子也稳。 特务看他一眼,没说话。 他站好后,望了一下天,没躲,没闭眼。 多年后,有人在北京西山为他立了雕像。


![[点赞]吴石将军案中,陈宝仓将军并没有暴露,而蔡孝乾也不知道陈将军是特工,陈](http://image.uczzd.cn/1794568748761564837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