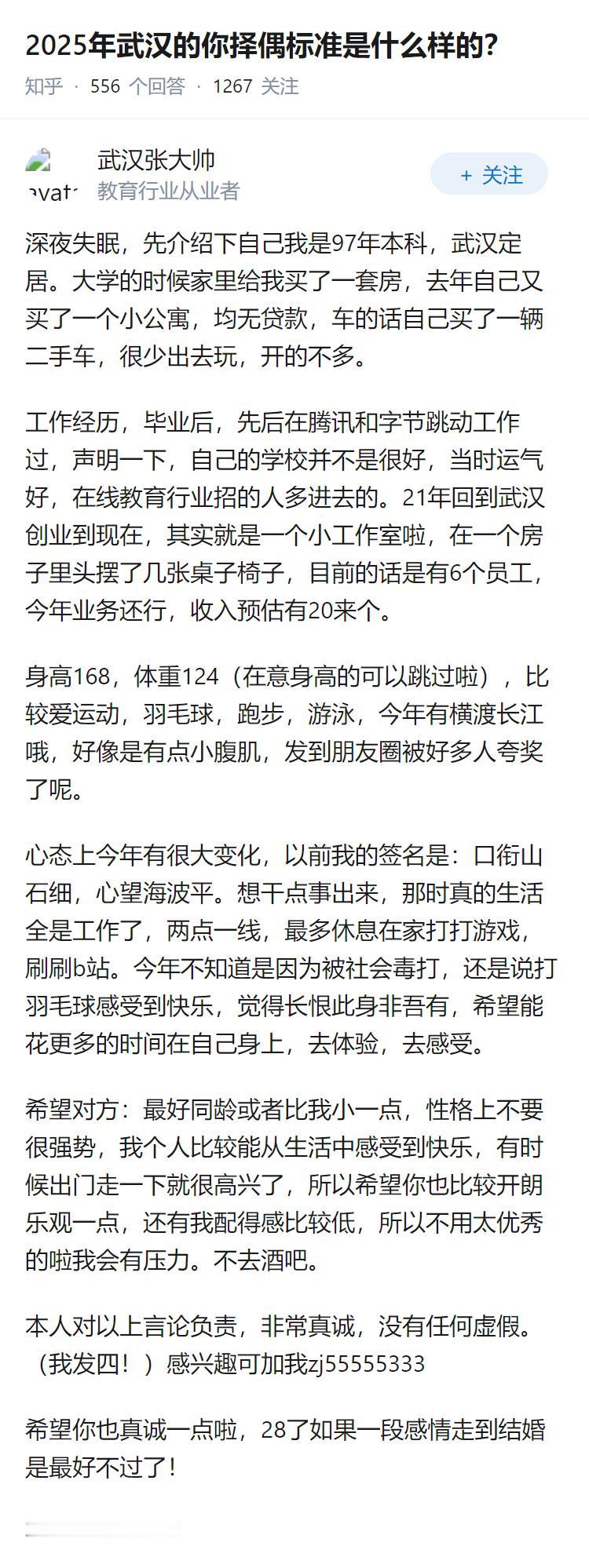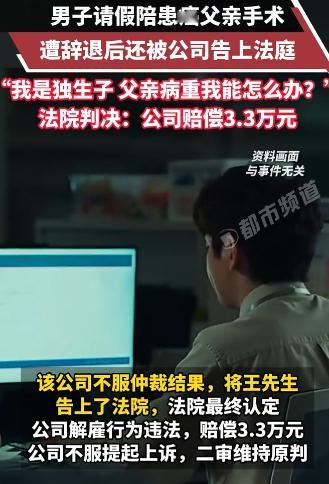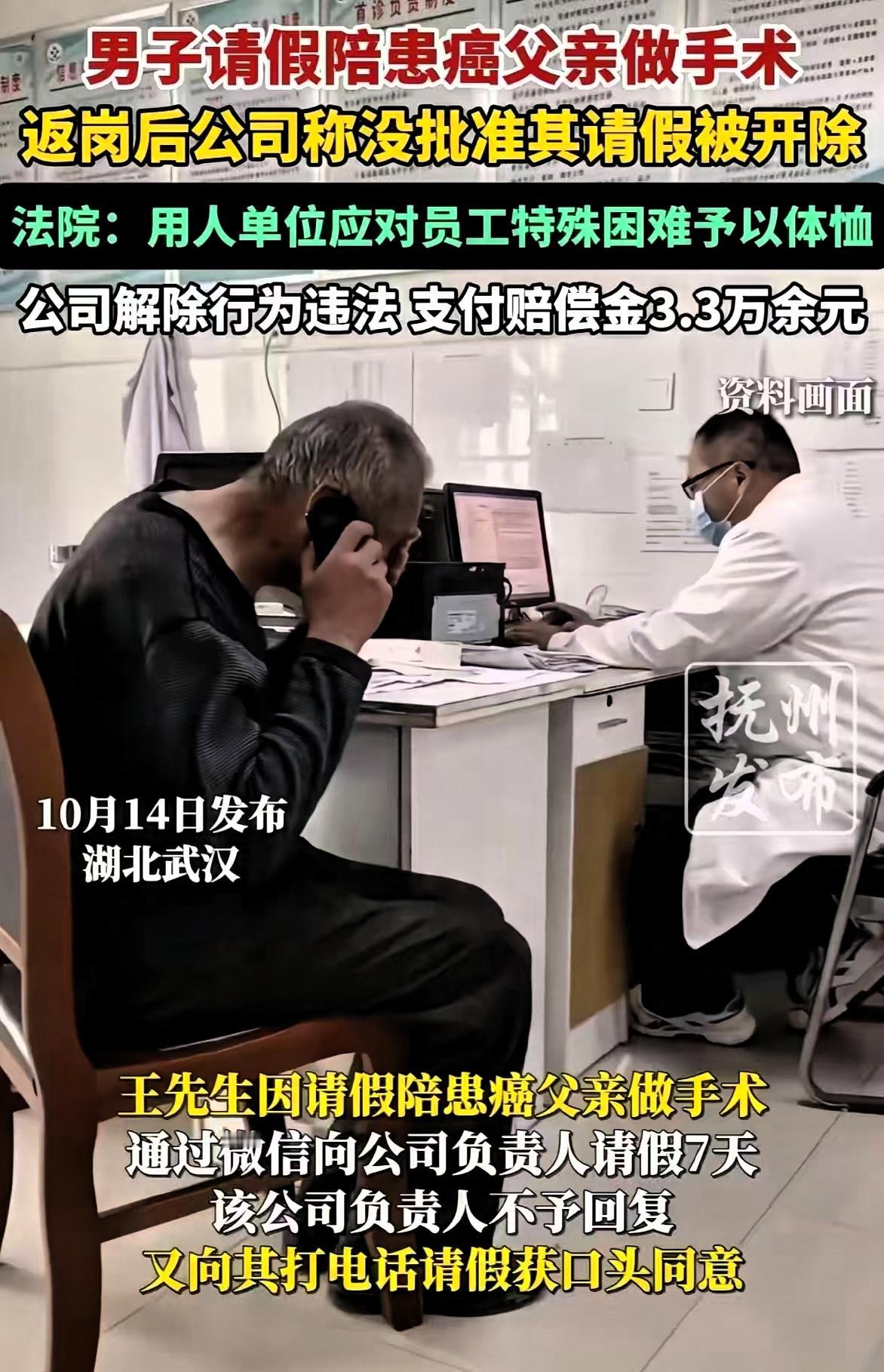《中国物流:从落后者到领跑者》[英]柯保罗(PaulG.Clifford)[加]罗甘(ChristopherLogan)著
吴幼喜杨达卿译中国财富出版社有限公司
近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非驻校高级研究员柯保罗(PaulG.Clifford)等出版著作《中国物流:从落后者到领跑者》,深入剖析中国物流业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探讨中国物流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中国物流:从落后者到领跑者》第一作者柯保罗,以及第一译者、中国物流学会常务理事吴幼喜。吴幼喜认为,中国物流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在吴幼喜看来,现代物流的发展方向将是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武汉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多项国家政策赋能和花湖机场这一国家级战略设施,正在成为推动这一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

10月9日晚,一架西班牙籍货机正在花湖机场装载货物。长江日报记者史伟摄
两位物流专家的破壁合作
吴幼喜与柯保罗相识的契机,要追溯到20多年前,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准备重组上市时。
那时吴幼喜在中国外运工作,负责集团战略管理与研究,正赶上公司筹备香港上市的关键节点——作为中国首家计划境外上市的物流企业,中国外运身上背着老国企的历史包袱,业务庞杂、员工机构冗余、效率低下。
为了拿出最佳重组方案,公司决定聘请国际咨询团队。当时麦肯锡等公司已开始布局中国,但他们最终选了柯保罗博士领导的美世管理咨询公司。柯保罗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曾在北京大学进修,自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在中国工作,在多个产业领域拥有深厚的管理和实践经验:曾带领团队为中国多家大型国有物流企业的重组和战略规划提供咨询服务,也为外国物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建议,为在华外国投资者解决跨多个行业的供应链问题提供支持。
吴幼喜作为公司与咨询团队的对接人之一,常和柯保罗泡在会议室,聊得最多的是“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
西方专家中,柯保罗是少有的熟悉中西方企业历史文化差异的人,他为多家中国企业做过咨询,既懂西方成熟的物流模式,又熟稔中国企业的“脾性”。
柯保罗领导的团队与中国外运决策层经过充分讨论,统一思想,决定将公司业务划分成核心业务和支持性业务,集团分割成上市公司和存续公司,以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为目标,借鉴国际流行的轻资产模式,打造现代物流和资本市场双轮驱动发展格局。吴幼喜作为境外上市工作组副组长深度参与了这一进程,与柯保罗及其团队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建立了长久友谊。
武汉“天生就应做物流枢纽”
武汉是吴幼喜的故乡。大学毕业后,他工作了几年,之后考取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一路读到博士,然后进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做外贸财务管理工作。
工作数年后,吴幼喜调入中国外运。他曾去地方公司挂职,在江苏的中外运长江公司与一线同事一起跑业务、理流程,摸清物流行业最真切的运作情况;他还参与过雄安新区现代城市物流规划方案的筹备和设计,琢磨怎么把雄安的物流空间布局做得更合理……
吴幼喜对家乡武汉感情深厚。他眼里的武汉,是长江中游最亮眼的城市之一。它的区位优势明显:长江、汉江交汇,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立体交织成网,还是东西产业转移、南北物资集散的“中转站”,他认为武汉“天生就该做物流枢纽”。
对于武汉的物流发展,吴幼喜有自己的期待。武汉仅有区位优势还不够,他盼着武汉能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物流巨头”。“花湖机场是个好机会,依托它可能培育出做航空货运、高价值物流的世界一流企业。”吴幼喜说,物流是“后台产业”,平时不显山露水,但能实实在在带动经济——货物流动速度快了,企业愿意来落户,老百姓买东西也更方便。
对吴幼喜而言,物流是事业,武汉是乡愁,“希望家乡能抓住机会,把区位优势变成真正的物流优势,在全国甚至全球物流格局里,能有更响的名头”。
[以下为《读+》与柯保罗的访谈]

柯保罗(PaulG.Clifford)
柯保罗简介: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非驻校高级研究员。曾先后任职于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现摩根大通集团旗下)、奥纬咨询公司以及美国网络企业思科系统公司。他在前作《中国悖论:站在经济转型的前沿》(2017年出版)中对华为进行了专题研究;近期,他与物流行业资深人士克里斯托弗・罗甘(ChristopherLogan)合著新书《中国物流:从落后者到领跑者》。
世界正在研究如何效仿中国
读+:您曾提到中国物流从“落后者”变为“领跑者”。在您看来,这个转折点具体发生在何时?对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
柯保罗:中国的物流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追赶模式,然而,中国一些大的物流企业现在已达到世界级水平,少数企业,尤其是在电子商务领域,其创新能力已超越世界其他地区。
中国推动物流升级的大规模努力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过去五年,随着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在物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得到应用,这一转型进程加速。在电子商务领域,技术的应用是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世界正在研究如何效仿中国。
中国的数字平台比美国和欧洲的平台更广、更深,因为它们更全面地整合了数字支付,并在最后一公里到消费者门口的过程中提供了更强大的定制化和更好的消费者界面。
读+:您会如何描述今天中国物流变革的历史地位?
柯保罗:当前中国物流业的转型,代表了中国运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通过全国性政策和规划驱动的方式,来改造所有工商业流程乃至更多领域的流程。这是基于健全的经济和商业思维的做法。
当然,将中国的经济模式整体输出是很困难的。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不只是一种中国现象,世界将会研究它,并在某些方面很可能加以采纳。
[以下为《读+》与吴幼喜的访谈]

吴幼喜
曾经的“后台产业”,实现了从人工到智能的飞跃
读+: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才接触到“物流”这个词。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物流”,它在我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吴幼喜: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明白“物流”到底是啥。物流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围着客户需求转,把运输、仓储、信息传递、打包、简单加工这些事串起来,帮货物从起点到终点搞全套高效服务。这个过程不只是把货挪地方、临时存放,还得及时告诉客户“货到哪儿了”“啥时候能到”,方便人家安排接货、生产或卖货,偶尔还做些增值服务,讲究快、准、全流程管理。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物流行业经历了从简单后勤服务到现代综合物流,再到互联网驱动下供应链物流的转变,每一步都与时代经济特征深度契合。
计划经济时期,物流尚未形成独立概念,更多以“后勤”形式存在,且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当时的后勤主要聚焦运输和仓储两大基础功能,还分为企业内部和社会外部两种服务模式。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拥有专属的车队和仓库,仅为自身生产服务,不向社会开放;而以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为代表的社会运输仓储企业,虽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但模式简单,大多只是在固定地点间往返运输原材料或产成品,几乎不涉及全程管理。在信息传递方面,也主要依赖纸质文件、电话和电报,整体服务仅作为产业或商业的配套,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市场经济对高效物流的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现代物流概念开始引入并发展。货运客户市场对物流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运输仓储,而是提出了综合一体化、高时效的要求。这一时期,欧美日等国家的第三方物流和及时配送(JIT)概念也伴随外资引进,为中国物流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经验以及机会,推动物流企业从传统作业迈向现代物流,为企业拓展全国乃至全球市场奠定了基础。
互联网的兴起和扩散打造了新时代的物流模式,让物流朝着供应链整合、智能化协同的方向发展,迈入新阶段。
物流企业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了对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仓储运输、销售配送等全流程的精准把控和效率优化。同时,电商物流、跨境物流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也让供应链物流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读+:您在译序中用“波澜壮阔的史诗”来形容中国物流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
吴幼喜:中国物流的发展历程堪称一部“从幕后走向台前”的产业演进史。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其从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后台产业”,通过持续的装备升级、技术革新与模式重构,最终实现了从落后到高效、从人工到智能的质的飞跃。
回顾发展初期,中国物流如同餐厅的“后厨”,长期处于台下作业状态。消费者关注的是商品本身,生产者关心的是产品销售,而连接两者的物流环节却鲜少被重视。当时的物流作业条件比较简陋:运输主要依赖敞篷卡车,仓库作业依靠叉车和大量人工搬运,整个物流作业过程既缺乏技术支持,也难以被外界察觉。
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中国物流开启了转型升级之路。在装备层面,运输工具从敞篷卡车逐步升级为集装箱卡车,并开始尝试智能化驾驶;仓储作业则从人工主导转向自动化、无人化,自动化分拣系统、智能库存管理等技术的应用,让货物处理效率得到质的提升。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商业模式的变革。早期以B2B(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为主的物流服务,仅连接工厂与商店,消费者需要自行提货。而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B2C(Business-to-Customer的缩写),物流首次直接面对海量的个人消费者。这一转变不仅打开了面向14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更让物流服务突破地域限制,实现了更广范围的服务覆盖。高效低成本的快递服务能力,则成为这一模式成功落地的关键支撑。
值得关注的是,物流领域的技术革新速度打破了传统认知。过去被视为制造业“跟随者”的物流业,在供应链管理的推动下,其智能仓储、无人配送等技术的应用水平已在某些领域不逊于甚至超越制造业。这个曾被认为门槛较低的行业,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快速转型。
中国物流的这场变革确实配得上“波澜壮阔”的评价。它不仅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更在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凤凰涅槃”,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精彩的缩影。
模仿西方起步,最终找到自己的路
读+:我国的物流业一开始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后来是怎样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形成了独特模式?
吴幼喜:我国物流业的发展起步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仿,早期与跨国外资物流企业合资合作,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过程降低了初期发展的资本与创新成本,是产业起步阶段的必然选择。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本土市场成熟,物流业逐渐突破模仿框架,结合自身市场需求与消费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围绕本土消费需求构建“高时效、强适配”的电商物流体系。中国消费者对物流时效性的高要求(如希望商品半天、一天内送达),以及“双十一”“618”等集中促销活动催生的“天文数字级”订单,倒逼物流业进行技术与运营创新。为应对海量订单的分拣、配送需求,物流企业大规模建设自动化仓库、无人化分拣中心,用机器替代人工完成商品挑拣、面单粘贴等环节,彻底摆脱了传统人工操作的效率瓶颈;同时整合公路、铁路、航空运输与仓储资源,打通“最后一公里”配送,形成覆盖全国的高效供应链,实现了“从几千公里外快速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服务能力——这种以电商为核心、适配集中消费场景的高时效物流模式,在西方市场较为罕见,是完全基于中国消费文化形成的创新。
另一方面,我们依托“一带一路”开辟“多通道、抗风险”的国际物流新途径。我国对外贸易物流高度依赖海运(占比超80%),但海运航线受国际地缘政治影响大,且主要服务于欧美日等传统市场。为分散风险、拓展新兴市场,我国首次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新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在海运仍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陆路运输,形成“海运+陆路”的多通道模式;同时对接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在当地投资建厂、配套物流服务,既为中国商品打开新市场,也帮助这些地区发展消费市场。
这种兼顾风险分散与新兴市场开拓的战略布局,突破了西方物流业“重海运、轻新兴市场”的传统思路,其所形成的物流模式成为我国国际物流的独特优势。
读+:您如何评价中国现代物流业在全球物流业中的发展水平?
吴幼喜:中国现代物流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规模领先、质量待升”的显著特征,整体处于“大而不强”的发展阶段,可从规模优势与现存差距两方面来看。
从规模维度看,中国物流业已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一“第一”主要基于全社会物流业收入与货运相关规模指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庞大的制造业产量直接带动物流需求,海运、空运、陆运及仓储等环节的总收入与货运规模同步增长,形成了全球领先的物流市场体量。这种规模优势虽与中国人口基数、市场需求有关,但核心驱动力仍是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两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发展质量与效率维度看,中国物流业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差距,尚未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一方面,在效率指标上,我国人均吨公里效率不及美国,人均冷库占有面积、仓储管理整体水平、能效标准也落后于欧美;尽管部分头部物流企业的仓储管理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但行业整体呈现“先进企业少、中间状态多、落后企业仍存”的格局,偏远地区仍有仓库依赖肩背手扛、板车等传统工具作业。
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合理性上,我国多式联运发展滞后,尤其是铁路在长途物流中的利用率较低——理论上600公里以上的长途货物更适合通过成本更低的铁路运输,但我国70%的货物(包括千公里级长途货物)均依赖公路运输,而公路本应更侧重短途、城市内运输,这种不合理的运输结构进一步拉低了行业整体效率。
目前,中国物流业规模领先,质量追赶尚需一段时间,但距离不是很远了。
武汉要成为包邮区,先要成为“成本洼地”
读+:武汉正在打造国家物流枢纽。以您的眼光看,鄂州花湖机场的崛起,对武汉乃至中国物流格局意味着什么?
吴幼喜:鄂州花湖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它的崛起不管对武汉打造国家物流枢纽,还是对整个中国物流格局调整,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武汉本身具有优越地理区位优势,工业基础扎实,光电子、生物制药、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产业发展迅速,市民文化具有重商的传统,但这些优势目前还没有完全转化成物流竞争力——城市在周围区域内的货物集散能力不强,辐射区域不广,至今没有真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物流企业和行业领军人物。
花湖机场是全国首个以顺丰(国内顶尖快递企业)为主体的专业货运机场,这正好能补上武汉物流的短板。它走的是航空货运路线,速度快、时效性强,特别适合高价值和时效性货物运输,要是未来相关部门能开通更多国内国际航线、建立高效的航空货运地面配套服务、统筹建设优良的武鄂黄黄区域营商环境,武汉就可能以花湖机场为中心,成为重要的国内外航空货物集散地。
花湖机场的横空出世也有利于整合本地的运输资源,进一步强化武汉作为国内重要交通枢纽节点的定位,如航空和公路、铁路等货物的衔接和转换,为武汉多式联运业态的模式创新和发展提供关键的支撑。比如像武汉已经开通的从俄罗斯到整个欧洲的国际多式联运航线,有了机场加持,货物集散能力会更强,能让货物运输更灵活。
花湖机场也填补了中部地区专业航空货运枢纽的空白,形成“东有上海、南有深圳、中有武汉”的航空货运格局,更好地衔接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
对普通人来说,花湖机场带来的变化也很实在。以后在武汉买东西,不管是国内其他地方的土特产和时令商品,还是国外的商品,品类会更丰富,配送速度也会更快,比如生鲜能更快送达,新鲜度更高;武汉本地的特产,通过机场运往全国乃至全球也会更便捷,更快到达消费者手中。
读+:我们网购时经常会看到“江浙沪包邮”的提示。我国为何不能实现所有地区都包邮?武汉作为物流枢纽,能算包邮区吗?
吴幼喜:先说说为啥全国不能都包邮。首先得有足够大的订单规模,像江浙沪一带,消费者群体庞大,每天下单量特别多,物流企业能凑够足量的货物。咱们都知道“买得越多越便宜”,货物量上去了,单件物流成本就降下来了,商家才敢承担运费搞包邮;要是像一些偏远地区,订单量少、需求不稳定,可能一天就几十件货,物流企业凑不够量,运输成本降不下来,不管是商家还是物流方,算经济账都不划算,自然没法包邮。其次是基础设施和固定专线,江浙沪有发达的汽运专线、铁路线路,这些线路像日常班车一样固定运作,运营效率高,成本可控;但很多地区没有这样密集的固定专线,运输得绕路或者等凑够货才走,时间长、成本高,也支撑不了包邮。
目前来看,武汉还没完全成为像江浙沪那样的全域包邮区,但有成为包邮区的潜力。武汉有地理优势和正在发展的物流硬件,也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和消费市场,能吸引周边河南、湖南、安徽等地的部分货物聚集;但也要看到,武汉还没形成“成本洼地”,要实现包邮,得让物流成本比周边地区低,比如从武汉发往各地的运费,比从当地直接发更便宜,这样商家才愿意选择从武汉集散货物、搞包邮。现在武汉周围还有竞争——比如郑州、成都、重庆都有货运机场,京东在南通也有货运机场,这些地方都在抢物流资源,武汉要拿出更有优势的成本和服务,吸引足够多的货量和订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