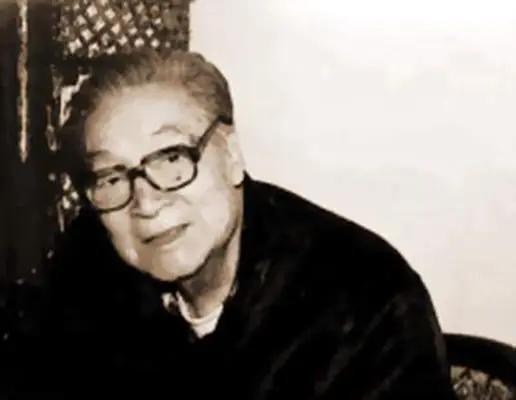2005年,作家冯亦代在临终之际,抓着妻子黄宗英的手,求她:“能不能把我跟原配葬在一起?”没想到,黄宗英却哭着说:“我陪你12年,还是不如她?”不过哭完黄宗英还是同意了。 1998 年冬,北京的深夜,黄宗英帮冯亦代整理枕头。指尖触到硬壳物件,翻出一看是张老照片 —— 郑安娜笑坐在上海弄堂的藤椅上,手里拿着译稿。 照片背面是冯亦代的字迹:“1940 年秋,安娜改完《老人与海》第三章”。黄宗英轻轻摩挲照片边缘,没叫醒熟睡的冯亦代,只是把照片放回原处,压在他常用的英文词典下。 1938 年上海,英文剧社的后台,冯亦代帮郑安娜递水杯。 郑安娜刚排完《罗密欧与朱丽叶》,擦着汗说:“你上次译的那段台词,‘爱不是时光的玩偶’,我改了两个字。” 她从口袋里掏出纸条,上面写着 “玩偶” 改 “傀儡”,旁注 “更贴悲剧感”。冯亦代接过纸条,手指和她的指尖不经意碰到,两人都红了脸,慌忙移开目光。 1941 年战乱中,冯亦代和郑安娜挤在逃难的火车上。郑安娜把冯亦代的译稿裹在棉袄里,生怕被雨水打湿。 “要是译稿丢了,我们再重译,只要人在就好。” 她靠在冯亦代肩头轻声说。冯亦代紧紧攥着她的手,看着窗外掠过的废墟,在心里默念:这辈子要和她一起译完所有想译的书。 1991 年郑安娜走后,冯亦代把他们合译的残稿锁在木盒里。每天清晨都会打开木盒,摸一摸残稿上郑安娜的批注,像在跟她说话。 有次整理书房,他翻到当年郑安娜改的台词纸条,突然蹲在地上哭了 —— 纸条边缘已经泛脆,却还留着她的笔迹温度。从那以后,他把纸条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 1994 年北京作协的茶话会,黄宗英主动跟冯亦代搭话。“您译的济慈诗里,有几处韵律,和郑安娜先生的风格很像。” 她递过自己的读书笔记。 冯亦代愣住,这是郑安娜去世后,第一次有人精准说出她的翻译特点。两人坐在角落聊了一下午,从济慈聊到海明威,从翻译技巧聊到各自的生活,越聊越投缘。 1996 年冯亦代生日,黄宗英送他一本新的海明威原著。扉页上写着:“愿我们能一起,续完你和安娜未竟的译事”。 冯亦代翻开书,看到里面夹着张便签,是黄宗英模仿郑安娜的批注风格,改了他之前译稿里的一个词。“你怎么知道安娜的习惯?” 他问。 黄宗英笑着说:“我翻了她的翻译笔记,也问了当年认识她的朋友。”2005 年中秋,冯亦代躺在病床上,拉着黄宗英的手。 “我走后,把我和安娜葬在一起,好不好?” 他声音微弱,眼里满是恳求。黄宗英的眼泪掉在他手背上,却还是点头:“我知道,她在你心里的位置,谁也替代不了。” 冯亦代笑了,从枕头下摸出那张郑安娜的照片,放在两人中间:“你看,安娜笑得多好。” 2006 年春,黄宗英去苏州选墓地。特意挑了块能看到湖的地方,跟郑安娜照片里的上海弄堂一样,有开阔的视野。 下葬时,她把冯亦代钱包里那张台词纸条,和郑安娜的译稿残页一起,放在骨灰盒旁。“你们终于能一起接着译稿了,” 她轻声说,“我以后常来看你们。” 2010 年黄宗英病重,躺在医院里还翻看冯亦代的译稿。跟护士说:“等我好点,要把他和安娜没译完的部分,再整理一遍。” 去世前几天,她让家人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放在冯亦代的英文词典旁边。“这样,我们三个的念想,就都在一起了。” 如今,上海作协纪念馆里,冯亦代的英文词典、郑安娜的译稿残页、黄宗英的读书笔记摆在一起。 年轻译者们看着这些物件,总能想起三段交织的深情 —— 冯亦代对郑安娜的念念不忘,对黄宗英的依赖信任;黄宗英对冯亦代的理解成全,对郑安娜的尊重体谅;郑安娜对冯亦代的默契陪伴,早已刻进时光里,成了最温暖的印记。 每年春天,都会有人在苏州的墓地旁放一束花,既是怀念,也是祝福,祝福这三段深情,在岁月里永远温暖。 参考资料: 《毛姆短篇小说经典集》冯亦代译 《冯亦代散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