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回忆,他领导不了父亲的老臣。他讲了一件事,有一年春节吴俊升来拜年,家里的孩子们自然也要给长辈拜年。吴俊升自然准备了红包,一人5000银行本票。 五千块!在当时是什么概念?这么说吧,1920年代,北京一个普通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三四十块大洋。一个警察月薪8块,大学教授撑死了也就三百来块。吴俊升一出手,就是一个教授一年多的工资。这红包,烫手。 孩子们可能还不太懂,但旁边的大人脸色都变了。这钱,给得太多,太重,已经超出了人情味儿,带着点别的意思了。是显摆自己有钱?还是想用钱在帅府的下一代身上砸出个更深的“干爹”烙印? 张学良当时就在边上站着,他说他看得“毛骨悚然”。他看着他爹张作霖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 张作霖没去碰那几张本票,他盯着吴俊升,开口了,话不重,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吴大哥,你这是干啥?过年,孩子们给你磕头,你给钱,行。但你给这么多,不对劲儿。” 吴俊升一愣,赶紧陪笑:“大帅,我的钱,我的一切,还不都是大帅你给的?” 这话听着是拍马屁,是表忠心,但在张作霖这儿,恰恰踩了雷。 “你说的是真话?”张作霖的声音沉了下去。 吴俊升看着大帅的脸色,心里咯噔一下,但嘴上还得硬撑:“那还能有假?” “好,”张作霖一字一顿,“你可要说真话。既然你这么说,这钱,你别给他们。你啊,回到黑龙江,给我好好地做事,别让黑龙江的老百姓在背后骂我张作霖的祖宗!” 这话一出,满屋子鸦雀无声。吴俊升“噗通”一声就跪下了,当场就给张作霖磕了个头,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张作霖的“雄才”,他处理的不是一个红包,是人心,是规矩,是权力边界。他一句话,就把吴俊升这种江湖气的豪爽,拉回到了“大帅与封疆大吏”的政治轨道上。他告诉吴俊升:你的钱,你的权力,源头在我这里;你要表忠心,别对着我儿子,去对着你治下的百姓,因为他们的口碑,才是我张作霖的脸面。 这一幕,给年轻的张学良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他明白,他爹和这帮老臣之间,有一套独特的“江湖密码”。他们可以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称兄道弟,但一到正事上,谁是王,谁是臣,那条线,比什么都清楚。张作霖用的是一种源自草莽,又超越草莽的智慧在驾驭他们。 可这套密码,张学良学不会,也用不了。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过的,是一个庞大但裂痕丛生的摊子。他面对的,是同一批人。吴俊升在皇姑屯跟着张作霖一起被炸死了,但还有杨宇霆,还有张作相,还有汤玉麟……他们名义上喊他“少帅”,心里怎么想的,就复杂了。 在他们眼里,张学良是“少主”,但更是个“孩子”。他们是看着他长大的叔叔大爷。这种亲情和江湖义气,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是凝聚力的粘合剂;张作霖一死,就变成了新权威的腐蚀剂。 就说杨宇霆吧。这个人跟吴俊升那种粗豪的武将完全是两路人。他自诩“儒将”,生活简朴到近乎刻板,据说在家吃饭顿顿离不开咸菜大酱。他能力极强,是奉系的“诸葛亮”,但为人也极其自负和刻板。连吴俊升为自己家的佣人求情,让他通融一个犯错的工人,他都当面顶回去,说:“你来晚了,已经处理了。” 这种人,张作霖能用,因为张作霖的权威能压得住他的傲气。张作霖欣赏他的才华,也能敲打他的野心。但张学良不行。杨宇霆仗着自己是“托孤重臣”,在很多事情上对张学良指手画脚,甚至摆出长辈教训晚辈的姿态。他跟常荫槐一唱一和,要成立什么“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几乎是要架空张学良。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学良能怎么办?他没有他爹那种“一句话就让你跪下”的威望。他不能像他爹对吴俊升那样,用几句敲打人心的话就把事情摆平。他跟杨宇霆之间,没有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过命交情。 所以,他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无奈的办法——枪。 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一声枪响,杨宇霆和常荫槐倒在血泊里。张学良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最高权威。但这恰恰证明了他权威的“不足”。真正的权威,是让对方心服口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张学良晚年回忆这件事,口气里满是感慨。他是在说,他爹的那一套,他学不来。他所受的现代军事教育,他所向往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和他爹那帮老臣们的江湖规矩、人情世故,格格不入。 今天我们回看这段历史,通过《张学良口述历史》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能更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轻统治者的困境。他想做一个新时代的领袖,却被旧时代的关系网牢牢捆住。他想摆脱父亲的影子,但他的权力恰恰又完全来自于父亲的这笔遗产。 那个五千块的红包,就像一个历史的隐喻。张作霖能把它轻飘飘地推回去,化为一句更有分量的政治敲打。而张学良面对的,是无数个比这红包更复杂、更棘手的人心难题,他推不开,也接不住,最终只能选择把它连同送礼的人一起打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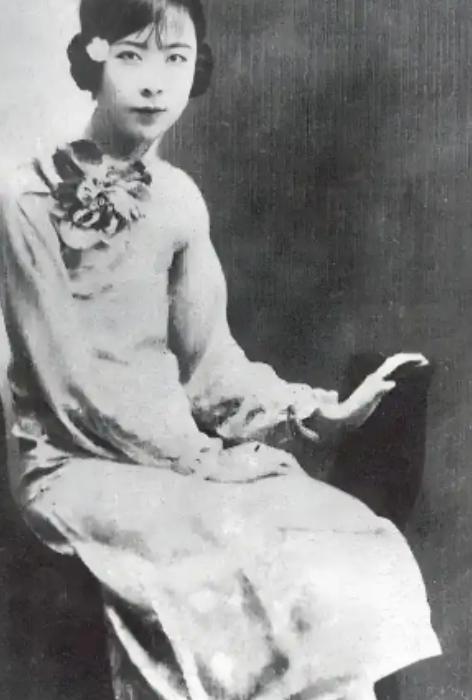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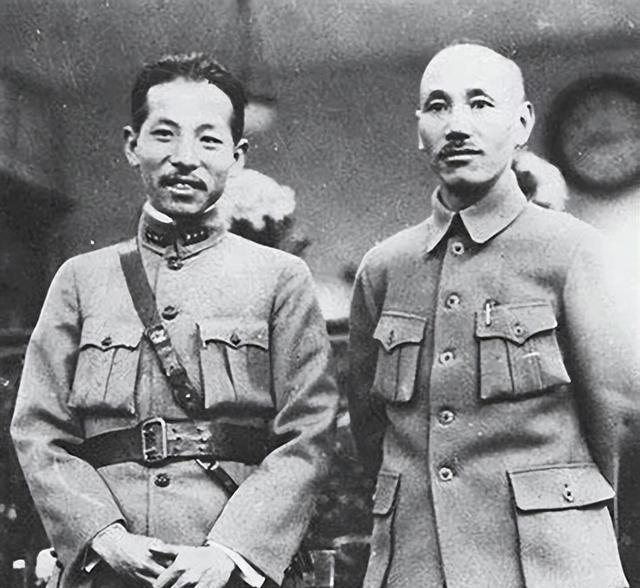



打铁
瞎基吧扯犊子,吴俊升会在这种情况下给张作霖下跪磕头?
战争2013 回复 10-18 04:45
不获得张作霖的谅解,只要派人去查吴俊升的账,能要其命,就是贪污。跪下就不查了,这事就过去了,钱拿回去就完了。
陈春秋a
压岁钱和磕头的事你是从哪里看到的。张学良回忆录的哪一部分?
战争2013
张学良确实政治才能不足,分不清私事和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