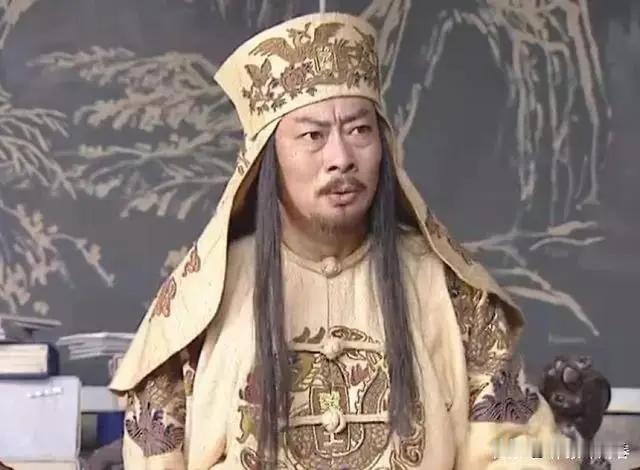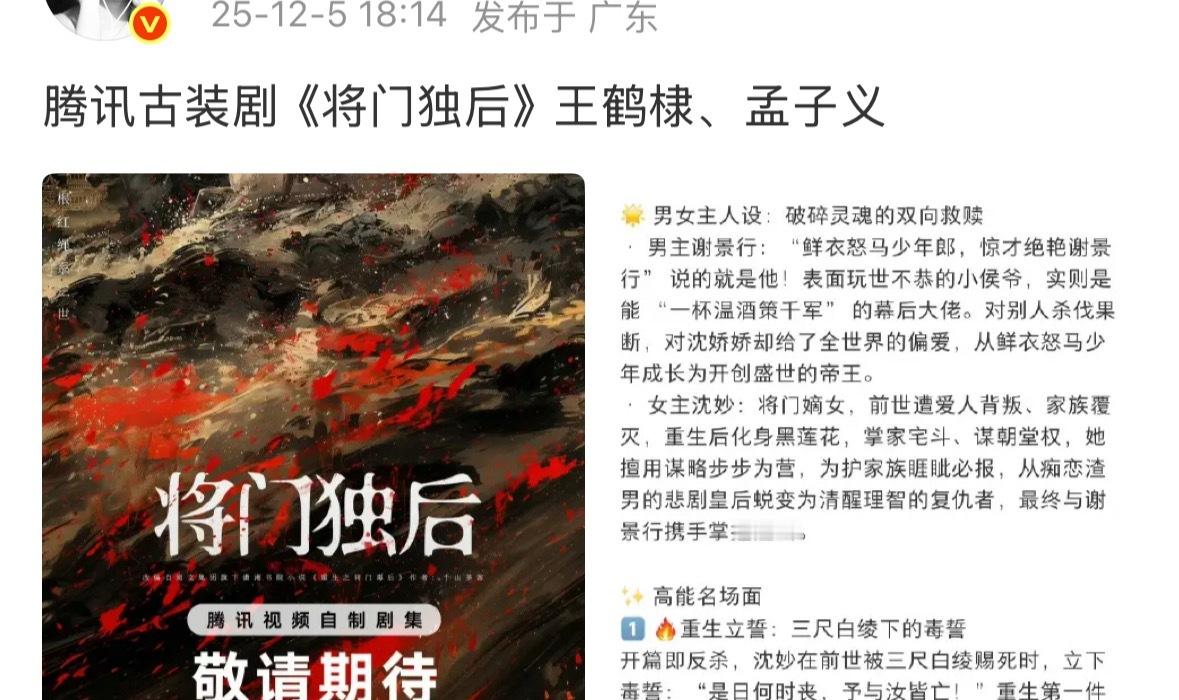1464 年,明英宗朱祁镇躺在龙床上,气息微弱眼看就要咽气,却突然撑着最后一口气下令:废除朱元璋定下近百年的后妃殉葬制,还把朱棣关了五十多年的建庶人朱文圭放出来。大臣们急得直哭:“皇上,您这是要拆祖宗的庙啊!” 他却咧嘴一笑:“老子快死了,就想让人记得我当过‘人’。” 提起朱祁镇,多数人先想到“土木堡之变”——1449年,他轻信宦官王振,亲征瓦剌被俘,几十万明军精锐覆灭,京城险些沦陷。这场惨败让他成了“昏君”代名词,可被俘和幽禁的经历,却悄悄改变了他的认知。 他在瓦剌当俘虏时,曾陷入困境,靠随从袁彬舍身护佑才存活;复位后被弟弟景泰帝囚禁南宫七年,靠太监阮浪等亲信偷偷输送物资度日。 这些低谷让他看清了皇权的脆弱和人性的可贵。被俘期间,他看到瓦剌贵族为争夺财物互相残杀,也见证普通士兵对家人的牵挂;南宫幽禁时,他与皇后钱氏相濡以沫,钱氏甚至哭瞎一只眼睛、跪瘸一条腿为他祈福。 大臣们反对废除殉葬,并非无理取闹——这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朱元璋驾崩时,有46名无子嗣妃嫔殉葬;朱棣去世,30名妃嫔从死;就连号称仁厚的朱高炽、朱瞻基,也各有5名、10名妃嫔殉葬。殉葬时,妃嫔或被缢死,或被灌毒酒,场面惨烈。 很多人误以为朱祁镇废除殉葬是受钱皇后单方面影响,实则核心是他对“皇权碾压人性”的深刻反思。 他亲眼目睹先帝(明宣宗)驾崩时妃嫔殉葬的惨状,其中宣宗贵妃郭氏的殉葬场景让他尤为震撼。 朱祁镇曾私下对内阁首辅李贤说:“先帝崩时,妃嫔从死者,朕每念及,心有不忍。” 这种“不忍”,源于他自身曾沦为“皇权牺牲品”的经历——土木堡之变后,他被瓦剌当作筹码,回京后又被弟弟幽禁,深知身不由己的痛苦。 废除殉葬的影响远超想象。它不仅让明朝后续皇帝不再推行殉葬,还影响了藩王宗室——《明宪宗实录》记载,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明确下令“宗室亲王去世,妃嫔无子嗣者免殉葬”。直到明朝灭亡,再无大规模后妃殉葬事件,这一决策拯救了上百位女性的生命。 释放朱文圭,比废除殉葬更具政治风险。朱文圭是建文帝朱允炆的次子,1402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后,将仅2岁的朱文圭囚禁在凤阳广安宫,号称“建庶人”,这一关就是62年。 朱文圭被释放时已64岁,长期幽禁导致他“不识牛马,生活难以自理”,完全与社会脱节。 大臣们反对,是担心“建文旧臣借机生事”。可朱祁镇的考量更深远:靖难之役过去60多年,建文旧势力早已消散,囚禁一个毫无威胁的老人,只会让天下人觉得皇室“刻薄寡恩”。 他对大臣说:“文圭辈皆先帝血脉,久幽禁可悯。” 这话背后,是对皇室内部残杀的反思——他自己曾被弟弟幽禁,更能体会“骨肉相残”的痛苦。 这一决策的政治意义重大。释放朱文圭后,朱祁镇下令“给其房舍、奴婢,许婚娶”,还赦免了建文旧臣的后代。 消息传出后,“江南士民皆称上仁”,尤其是建文旧臣后裔,对皇室的敌意大幅消解。这不仅修复了靖难之役留下的历史伤痕,更稳定了统治基础。 最常见的误区,是将这两个决策归为“临终良心发现”。实则早在复位初期,朱祁镇就已显露“人性觉醒”的迹象:1457年复位后,虽未直接为于谦平反(于谦平反由其子宪宗朱见深完成),但也未株连其家人,还释放了于谦之子于冕;1461年平定曹石之变后,只惩处首恶石亨、曹吉祥等人,未牵连无辜。这些举动,都与他早年的浮躁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人认为朱祁镇“昏庸一生,只做了这两件好事”。这种评价过于片面:他虽有土木堡之变的惨败、错杀于谦的污点,但复位后重用李贤、彭时等贤臣,惩治石亨等奸佞,政治渐趋清明;同时整顿吏治,减轻赋税,还限制了锦衣卫校尉随意缉捕官员的权力。 朱祁镇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是葬送大军、错杀忠臣的“昏君”,也是平反冤抑、体恤底层的“仁君”;是被俘的“囚徒”,也是复位的“帝王”。 但临终的两个决策,让他超越了“昏君”或“仁君”的标签——他在皇权的巅峰,守住了“人”的底线。 朱元璋、朱棣靠殉葬彰显皇权威严,却留下“冷酷”的骂名;朱祁镇废除殉葬、释放囚徒,看似“拆祖宗的庙”,实则为皇室赢得了“仁厚”的口碑。这告诉我们:皇权的稳固,从来不是靠暴力和残杀,而是靠对人性的尊重。 今天再看朱祁镇,我们不必刻意美化他的“昏庸”,也不必夸大他的“仁厚”。但他临终的两个决策,确实让我们看到:即便是身处皇权顶端的帝王,经历过足够多的冷暖后,也能唤醒内心的人性。这种“记得自己是人”的清醒,正是朱祁镇在历史上最动人的光芒。 参考资料:盘点中国史上一生当过2次皇帝的6个牛人 明英宗朱祁镇——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