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在八宝山做了十几年引导员的远房表哥告诉我: 干这行见多了生离死别,真的悲恸不是靠声音大小来衡量的。他参与安排过不少文化老人的告别式,有些家属哭得站不住,也有人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沉。翁帆属于后一种。她站在亲属队伍第一个,一身黑衣服熨得平整,眼皮肿着,可腰杆一直没弯过。表哥原准备去扶的手,始终没递出去。 真正的伤心是往里走的,化成旁人看不真切的细处。 签到簿前她握笔写了三遍才写稳名字,写完把笔尖朝内轻轻摆正。向遗体鞠躬时,她身子晃了晃,旁边人想扶,她摇摇头,手指把袖口捏出了一道褶。这些动作不起眼,却是常年累月养成的分寸。 日子久了,体贴就成了本能。 杨先生最后几年走路慢,翁帆总落后半步跟着,手虚虚护在背后,不让他觉得被搀着。医院里插管说不出话,她举着小白板,他眼睛看到哪个词,她就顺着写下去,举到他眼前等他点头。告别式前夜彩排,她特意提醒把休息室的窗帘换成亚麻料子——透光柔和,不刺眼。这些小事堆起来,比什么解释都重。 子女们让她站头一个,不是做样子。 杨光诺签完到,自然退到她左后方半步。杨光宇鞠躬时,视线总是低垂着落在她鞋边。表哥说,一家人彼此的站位,手放的地方,比多少篇报道都真。仪式结束清场时,他看见翁帆大衣内袋露出半截旧银链子,坠子是个“宁”字。边角磨得发亮,21年的日子都在里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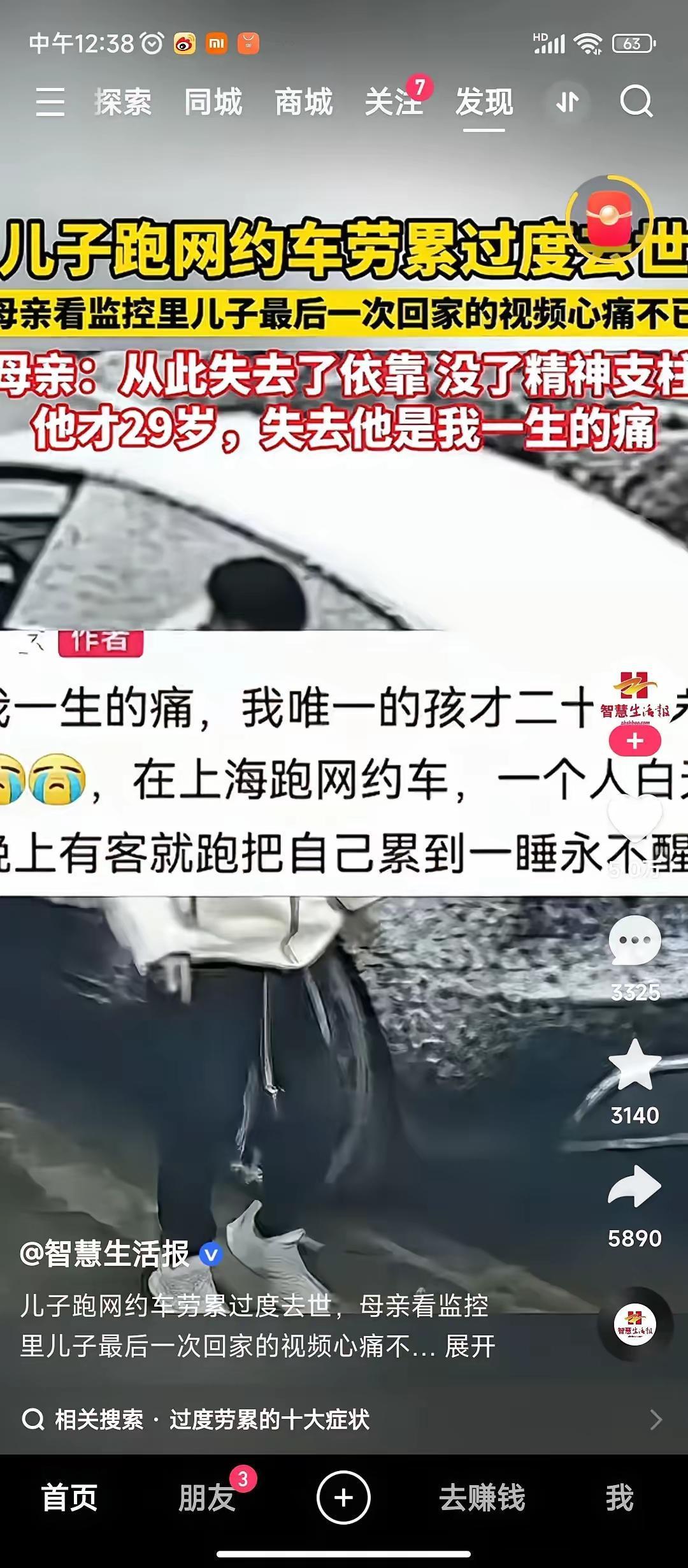


倪林
实在没什么东西写就早点休息
用户82xxx76
你这个远房表哥看得真仔细
真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