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阎连科提干成为一名副连级军官,战友给他介绍了一位军校女学员,还是县武装部长的女儿。在战友的鼓动下,他给女学员写了一封信,结果女学员回信说“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 阎连科是谁?他是从河南农村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他打小的愿望特朴素:吃饱饭,走出农村,娶个有城镇户口的媳妇。 怎么走出去?两条路。 第一条路,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他父亲发电报让他从水泥厂回家考试。他准备了四五天就上了,结果呢?全县考生集体落榜。 那就只剩第二条路:当兵。1978年,阎连科参军了。 在部队里,阎连科是真玩命。新兵连打靶100环,师里比赛拿第三,立三等功。本来因为枪法好,要被挑去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结果,又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来了,营部教导员爱文学。 这位教导员看了阎连科入伍前写的小说,大手一挥,把阎连科从前线名单上划掉,调到营部当了通信员。 后来,他被推荐到信阳的创作班学习,在《战斗报》上发了第一篇小说《天麻的故事》。一个新兵蛋子发小说,这在当时是“爆炸新闻”。他顺理成章被调到机关,入党,又立三等功。 1981年,上级发文件,明确要求“提干军官必须经过军校的培训”。 阎连科,没这个机会。 他死心了。老村长来信让他回家接任村长,父亲又病重,他一咬牙,办了退伍证。兜里揣着110块钱退伍费,给家人买了点东西,登上了回家的火车。 火车开动前,一辆军用吉普车直接冲上了站台。团长扒着车窗,扯着嗓子喊:“阎连科在哪?阎连科在哪个车厢?” 原来,他编的独幕剧《二挂鞭》在北京全军会演拿了第一。文化处的干部跟领导说:这帮优秀战士,演完就得退伍回家,太可惜了。 领导大笔一挥,特批了20个提干名额。阎连科是其中之一。 团长说:你退伍费都花了,车也上了,你先回家,7天后你还想提干,你就回来。不回来,名额作废。 回家后,又是挣扎。关键时刻,他那个在邮电局工作的姐夫,一句话点醒了他:“还是让连科回部队提干吧!人生的路接着往前走,不要回头。” 就这样,阎连科返回部队,换上了四个兜的军装。他终于,彻底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吃上了公家饭。 再回到1982年那封扎心的回信。 阎连科,一个刚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堪称“天选之子”的年轻军官,他心里该有多骄傲?他代表的,是那个年代靠着机遇、才华和“贵人相助”杀出来的草根精英。 可他遇上谁了?一个军校女学员,武装部部长的女儿。 她代表的,是1980年代正在崛起的“新精英”。 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的价值被重新捧上神坛。“军校学员”这四个字,在1982年,含金量甚至超过了阎连科这个“实战派”提干的副连长。 所以,那姑娘一句“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翻译过来就是:你那套“老黄历”的成功,我看不上。你有本事,按“新规矩”来证明一下自己。 这一巴掌,比在部队里挨个处分还难受。 它恐怕也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件事:时代变了。 光靠“提干”这个身份,已经镇不住场子了。 阎连科是怎么“考大学”的? 他没有再回去参加高考。但他用另一种方式,给自己办了个“大学”。 提干后,他有了更多时间。他把自己反锁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贪婪地”阅读。 后来,他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这算是他迟来的“学历”。 他开始疯狂写作。江湖传言他“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 但他自己后来反思,说那段时间的作品“千篇一律,没有灵魂”,心里浮躁,只想输出。 真正的蜕变,是在1991年,他因为写作得了腰突症,被迫停笔。病痛让他静下来,重新读那些经典,他才开始反思,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这才有了后来的《日光流年》、《年月日》、《受活》、《丁庄梦》。 阎连科后来拿了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拿这个奖。他在获奖演说里说:“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 他还写了《我与父辈》。 这本书的稿子,打字员是哭着打完的。打好的电子版发给阎连科的儿子,他儿子回了6个字:“看过了,掉泪了。” 新书发布会,本来在复旦。同济大学的校长看了书,哭得不行,强烈要求把首发仪式改到同济。 一个16岁的复旦附中女孩说:看完这本书,我知道如何来处理我和父母的关系。 一个作家,能写到这个份上,还需要那张“大学文凭”来证明自己吗? 阎连科曾直言:“我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把自己对那片土地的爱、恨、内疚,全写进了书里,写得太真,太狠。 他终其一生都在逃离故乡,但他的所有成就,都来自于回头凝视那片土地。 回头再想1982年的那个下午,那个军校女学员。她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当年那个“有本事让他去考大学”的激将法,无意中,竟“逼”出了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 阎连科用他的一生,回答了她的问题。他没去考那个狭义的“大学”,但他用自己的作品,给整个时代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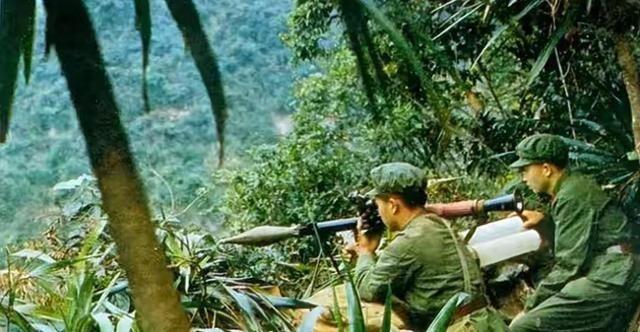


用户10xxx85
军校女学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