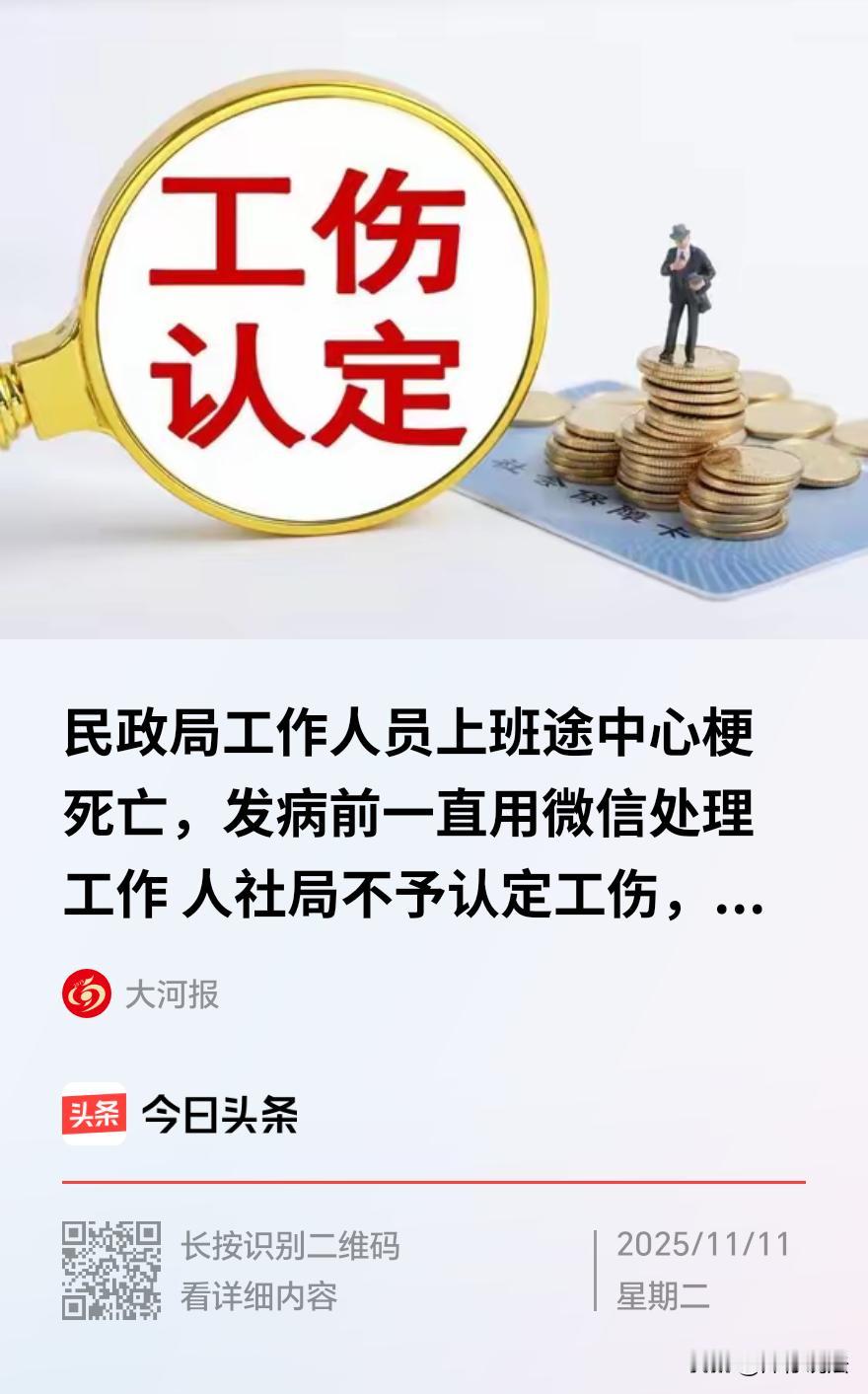辽宁辽阳,一男子在民政局从事工作,凌晨6点,刚出门准备上班,就收到领导微信询问工作安排,立即在手机上协调工作安排。不料,短短几分钟后,男子突发心梗倒在家附近的街头,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案发后,民政局向人社局申请工伤,人社局却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男子家属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决定,责令人社局重新审查。人社局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这样判决。 2024年7月17日,清晨5点多,史某像往常一样起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因家里离单位有一段距离,平时需要开车上班。 这天,史某计划先去单位处理一些事务,然后可能还要去下属单位出差。 史某在民政局工作多年,主要负责协调社区服务和活动安排,工作琐碎但责任重大。 近年来,随着微信等通讯工具的普及,史某的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办公室,下班后,他经常通过微信回复领导消息、安排任务,这几乎成了他的日常习惯。 早上6点整,史某刚洗漱完毕,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就响了起来,他拿起手机一看,是领导刘某丙发来的消息:“今天我应该几点到,还有谁去?” 这条消息看似简单,却涉及当天的工作安排,史某没有犹豫,立刻开始处理。 6点20分,史某回复领导:“我问问孙某。”同时,他将这条微信截图转发给了科室同事孙某。 孙某很快回复:“昨天我跟领导说没统一约,今天去不,你和领导。” 史某又追问了一句:“咱科里都是灯塔吧?” 孙某确认:“是。” 对话结束后,史某出门去取车,准备赶往单位,他家附近有一家超市,是他每天必经之路。 然而,就在史某走到超市附近时,突然感到胸口剧痛,呼吸困难,他勉强支撑着,但身体不听使唤,最终倒在了地上。 路过的好心人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点41分,医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遗憾的是,尽管医生全力救治,史某还是在当天不幸去世,死亡原因被确认为急性心肌梗死。 史某的妻子和子女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个平时身体还算健康的人,怎么会就这样倒在了上班的路上? 在整理遗物时,家人注意到了他手机里的微信记录,那些清晨的对话,让他们意识到,史某在发病前一刻,还在处理工作事务。 2024年8月13日,在家人敦促下,民政局向市人社局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 2024年10月10日,人社局在调查后,认为史某的死亡发生在上班途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范畴,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史某家人不服,遂一纸诉状将人社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撤销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在法庭上,人社局认为史某的死亡发生在通勤途中,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人社局还指出,史某的微信对话内容简短,属于临时性沟通,不足以证明是工作原因的直接导致。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法院指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不能局限于单位规定的上下班时段和固定的物理办公场所。如果职工的行为确系为了单位的利益,履行工作职责,那么其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就存在合理延伸的可能性。 本案中,史某在清晨6点03分收到直属领导刘某丙关于工作安排的微信询问,并于6点20分回复“我问问孙某”,并立即将问题转发给同事孙某进行协调沟通,这一系列行为是清晰、连贯的工作指令接收、反馈与协调过程。 该行为并非偶发的、与工作无关的私人社交,而是直接响应领导工作指令、解决具体工作问题的职务行为。 法院认为,在此时空背景下,史某通过微信处理工作,其身份是“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民政局工作人员”,其行为发生地无论在家、在途可以被认定为“工作岗位”的延伸;其行为发生的时段,可以被认定为“工作时间”的延伸。 此外,《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法院进一步指出,人社局未对史某平时下班后通过微信进行工作的情况进行审查,在事实尚未查清、关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作出了对职工不利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该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法院认为,人社局认定史某死亡不构成工伤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 人社局虽然提起上诉,但没有新证据及新事实。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