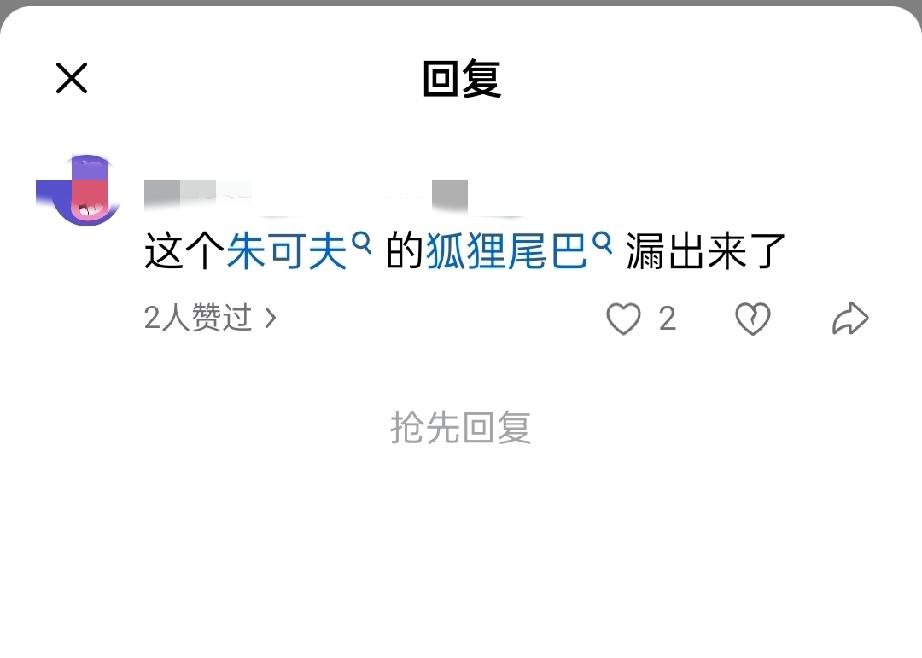这是1935年34岁张学良在西安的一张照片,都说张学良长得帅,这么看也不过如此! 往前翻,不得不从一九〇一年说起。 那年他生在辽宁海城的大帅府,父亲张作霖,脾气大,刀子快。 小小年纪,一边被塞进私塾认字,一边被拎进军营看刀光枪影。十六岁,母亲赵氏去世,家里一下冷下来了,他只好提早学会收拾烂摊子。教会学校带给他一点西式思路,军营又教会他怎么排兵布阵,两头拉扯,人也跟着长成了另一种模样。 二十岁那会,他跑去吉林剿匪,领一支骑兵在冰天雪地里追了三个月,最后把匪首活捉回来,“少帅”这个称呼就粘在身上。 奉系势力越做越大,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在东北攫取的那些“特殊权益”越扎越深。 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旅顺、大连,统统被对方当成自家后院。张作霖想在列强之间找平衡,终究顶不住。 一九二八年,皇姑屯的火车一声巨响,他死在日本人的炸药堆里。 二十七岁的张学良穿孝服站出来,接手东三省。 他说得不多,“你们把我父亲炸死,还想拿国家利益跟我谈,国恨家仇,一块算”,态度摆在那里。 一九二九年将近,他在沈阳宣布东北易帜,把五色旗收起,把青天白日旗升上来。形式上全国算是统一了一回,军阀混战压了下去。 他成了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中原大战里带东北军入关,让那场内战收了个不算太难看的场。 战功有,败账也有。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他为了收回铁路权益,同苏军对上,东北军一口气扔掉一万多条命在松花江边。 再过两年,中原大战里他连轴转,伤寒病落在身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里,沈阳城外炮声响起,他躺在北平协和医院,烧得迷迷糊糊。 军令传来“不抵抗”三个字,东北城池一块块被吞掉,热河很快也失守。 等他从病床上爬起来,对着地图发了三天呆,屋门反锁,谁喊都不应。外头骂声一片,“逃跑将军”“不抵抗”,一顶顶帽子扣上去,他嘴上不辩,心里却给自己记了死账:这辈子总得想办法把日本人赶出去。 一九三三年,日军进攻热河,他亲自上前线,打到最后还是守不住。 回到南京,当众把军装往桌上一放,辞职,背起行囊去了欧洲。 在德国,看着纳粹旗子一片片挂起来;在苏联,看着一个庞大机器轰隆隆运转。他明白得更透:靠一支东北军,护不住整个中国;这碗饭要想不被人掀翻,得全桌人一起端。 这一圈走完,一九三五年,他带着东北军进驻西安,挂着“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名头,干的是内战的活。他看着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一边是东北兵,一边是红军,心里明白这样打下去,便宜的是谁。 于是悄悄开始改旗换鼓。 派亲信去陕北见毛泽东,搭桥。 默许在西安搞东北救亡总会,鼓动士兵认清外敌。成立长安军官训练团,把抗日写进课程。 还派人去新疆找盛世才谈保住河西走廊,又琢磨着把自己一九二三年出钱办起来的东北大学往西安搬,将来好给抗战多留点读书人。 陕北那边,红军苦得更厉害。长征一路冲杀,七八万掉到几千,衣服破、肚子空。 中共中央给苏联发电报,说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乱印钞,张学良那边的钱也借得差不多。 前头叶剑英代表中央开口,他当场答应借三十万,先掏五万现钱,又答应去上海想办法筹二十五万。棉衣更急,他从库里拨出一万套,从西安送往兰州,让红军在半路接应。 后来陆陆续续,加起来借出的款有六十万,棉衣棉鞋、粮食弹药压根算不清。 苏联那笔援助说好十一月底到,到点没见影,他这边只好再挤出十万救火。张闻天发电,说你们多拖一天,前线就多冻死饿死一些人,这话听着扎心。 账算到这一步,他心里有数,只靠送钱送棉衣,救不了根。 国民政府那句“安内攘外”不翻过来,战场早晚还会对准自己人。一九三六年,他连着给蒋介石发了二十多封电报,苦口婆心劝把枪口调向日本。西安的雪夜里,他把二十三封电报烧成灰,只留四封揣在兜里,算是留个念想,也算给自己打气。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城外又是枪声。 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蒋介石。 张学良和杨虎城把局翻了个个,把本该打红军的兵力绕回来。蒋在山沟里被找到时,一身泥。他站在蒋面前,敬了个礼,手举到帽檐又放下,说今天犯上,不为私。 结果一张牌发出去,全桌的反应都变了味。 苏联顾着大局,让中共转向联合蒋,阎锡山那边权衡半天,收手当看客。 局势一步步滑到“和平解决”那一档。他咬牙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把自己当筹码。人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后半生就交代了。软禁从三十六岁开始,足足拖了五十四年。 东北军分崩离析,杨虎城后来连家带命一起赔进去。 这些年,他在雪窦山教看守拿旧轮胎做拖鞋,在井上温泉抓着《明史》做批注,字全往右歪,是当年做手术没麻醉留下的后遗症。 一九八八年,他被“免监”,问能不能回沈阳,得到的是摇头,只好改飞檀香山。 落地那晚,他去超市买了最便宜的酸菜罐头,用自来水冲了三遍,再煮一锅白肉酸菜,闻着勉强有点松花江的味道。 二〇〇一年,檀香山的小礼堂安放着他的棺木,灵车路过唐人街,华侨拿出一盘旧磁带,放起《松花江上》,声音发飘,副歌拖得像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