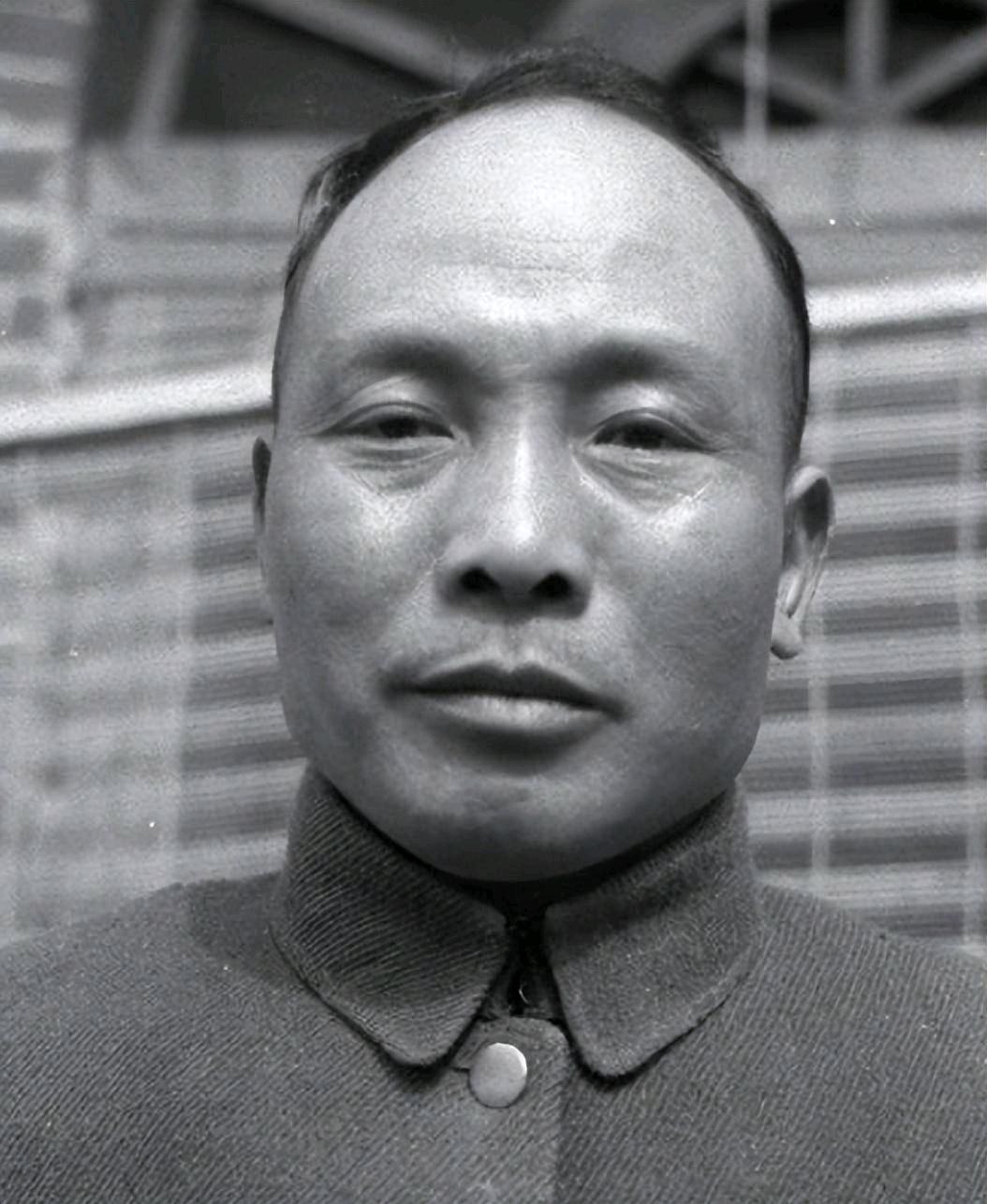1948年的寒冬,云南易门县的一间阴暗牢房里,潮湿的墙壁渗着水珠,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血腥的味道,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声划破死寂。被粗麻绳死死绑在刑架上的孙兰英 单薄的蓝布褂子早被血污浸透,冻得发紫的手腕被麻绳勒出深可见骨的血痕,可她紧咬的牙关愣是没松过半分,连呻吟都带着一股子硬气。敌人刚用烙铁烫过她的肩头,焦糊的气味混着潮气往鼻腔里钻,她却只是抬起布满血丝的眼,冷冷扫向对面面目狰狞的审讯官,干裂的嘴唇扯出一丝轻蔑的笑。 没人知道,这个看着不过二十出头的姑娘,已经在滇中大地的地下战线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年。她本是易门县一户普通农家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在县城求学的表哥偷偷给她塞了本进步小册子,册子上的字她认不全,可“为穷苦人翻身”的道理,却像种子一样落进了心里。后来县城来了地下党同志,她瞅着那些人冒着风险给百姓分粮、讲革命道理,二话不说就主动凑上去帮忙,先是帮着传递消息、印刷传单,十七岁那年,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入了党,成了易门县地下党组织里最年轻的联络员。 她的本事是在实打实的斗争里练出来的。那时候滇中地区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乡绅和伪保长勾连在一起,对地下党严防死守。孙兰英就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挑着担子走村串户,把传单藏在货筐的夹层里,把情报缝在衣角的衬布中。有一回她去山区送密信,半路遇上伪乡丁盘查,她急中生智,把密信混进给老乡带的草药包里,还笑着跟乡丁说“是给山里老娘治咳嗽的”,愣是凭着那份镇定和机灵蒙混过关。也正是这份能力,让她很快成了组织里的骨干,负责联络周边几个县的地下武装,筹备武装起义的前期工作。 这次被捕,是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起义筹备的关键阶段,那个被她当作亲弟弟看待的联络员,在敌人的糖衣炮弹下泄了密。她是在去和武装小队接头的路上被围的,突围时腿上挨了一枪,没跑多远就被按在了地上。敌人原以为抓了个年轻姑娘,随便吓唬几下就能撬开嘴,可他们没料到,这姑娘的骨头比钢铁还硬。 审讯室里的酷刑换了一轮又一轮,老虎凳压断了她的腿,竹签钉进了她的指甲缝,可她从始至终没吐露半个字的机密。敌人急了,把叛徒拉到她面前,想让叛徒劝降。看着那张曾经熟悉的脸,孙兰英眼里的轻蔑变成了刺骨的冷,她啐了一口血沫,哑着嗓子骂道:“你这软骨头,不配提‘革命’两个字!”叛徒被骂得面红耳赤,低着头不敢看她。敌人见劝降不成,又拿她的家人威胁,说要是不招供,就把她远在乡下的父母抓来。孙兰英的心猛地揪紧,可她转念一想,要是自己松了口,不仅起义计划会泡汤,更多战友和群众会遭殃,父母知道了,也绝不会原谅她的妥协。她深吸一口气,抬头对着审讯官喊:“要杀要剐随便你们,想从我嘴里套话,做梦!” 牢房里的寒气越来越重,她的意识开始模糊,可脑子里还清楚地记着组织交给她的任务,记着和战友们约定的起义时间,记着穷苦百姓期盼解放的眼神。她知道自己可能撑不到天亮了,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刑架的木头上,用指甲刻下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党”字。那字迹很浅,却像一道光,刺破了牢房的黑暗。 那个寒冬,孙兰英最终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没等到起义成功的那一天。可她用生命守住的机密,让后续的武装起义得以顺利开展,滇中大地很快燃起了解放的烽火。很多年后,易门县的百姓还会说起那个宁死不屈的孙姑娘,说她的骨头,比滇中的山还硬。 我们总说革命先烈的气节可贵,可这份可贵,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是对百姓的深切牵挂,是在生死抉择面前,毫不犹豫选择舍己为公的担当。那些嘲笑先烈“傻”的人,永远不懂这份“傻”里,藏着怎样的家国大义和人间情怀。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