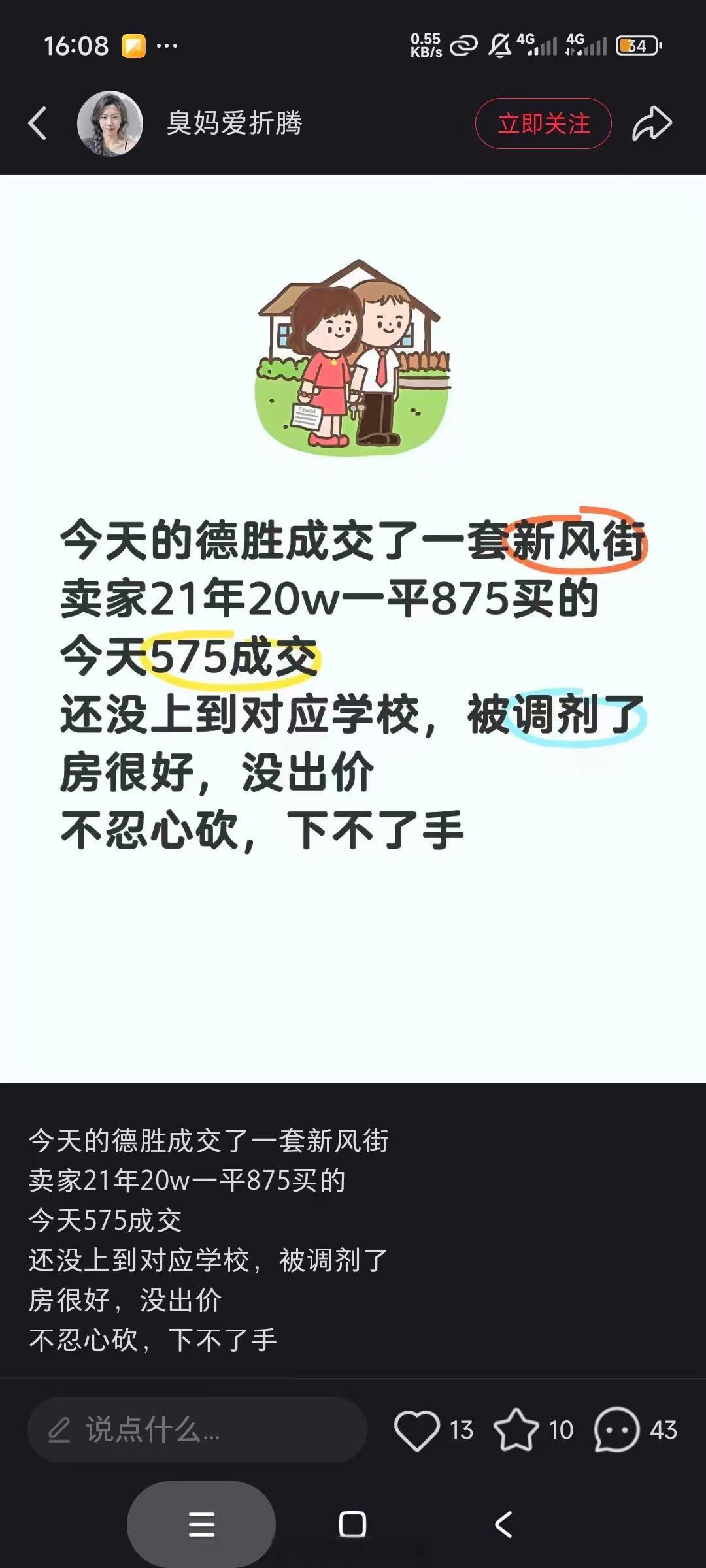昨天女主和我哭诉,说她这辈子挨了无数次打,受了一辈子气。 我是这个家的新保姆,来的那天推开厨房门,瓷砖上的油污结成硬壳,钢丝球擦过都能留下划痕,电饼铛的凹槽里卡着发黑的食物残渣,像嵌进骨头缝里的污垢。 她枯瘦的手指攥着衣角,突然猛地掀起袖口——小臂内侧青紫的瘀伤像陈年的旧茶渍,层层叠叠晕开,新伤的红和旧伤的紫混在一起,看得人心里发紧。 “婆婆在的时候骂了七年,走了以后他就动手,”她声音发颤,眼泪砸在我手背上,“身上就没好过,新伤压着旧伤,有时候疼得睡不着。” 男主后来和我闲聊,说这五年换过三个保姆,最长的干了三年多,最短的才半年,“有的手脚不勤快,有的太懒”,他皱着眉评价,像在说一件用旧的家具。 那些换过的保姆,真的都像女主说的那样苛刻吗?或许她们也在男主的挑剔下活得小心翼翼?女主记得最清楚的是上一个保姆,连她吃香肠吐皮都要管,转头就跟男主告状说她“浪费粮食”。 我没说什么,只是把蒸好的香肠切成小块,放在她面前的盘子里,轻声说“吐在这张纸上就行”。她愣住了,眼睛眨了好几下,才慢慢拿起一块,试探着咬了一小口。 包办婚姻像条看不见的锁链,她十八岁被送进这个家,婆婆在世时她忍了七年,以为熬到老人走就能喘口气,没想到丈夫的拳头比婆婆的骂声更重——她连回娘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只能在这个屋檐下挨着。 第一天搞卫生,我用掉三瓶油烟净。油烟机的滤网拆下来时,油水滴在地上汇成小水洼,擦到第三遍,手指关节都在发抖。现在不一样了,厨房的瓷砖能映出人影,衣柜里的衣服按季节叠得整整齐齐,女主每天早上都会摸一摸窗台,那里再也没有积灰。 她脸上的泪痕少了些,昨天甚至主动问我“明天能吃饺子吗”,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 我看着她手腕上淡下去的伤痕,突然觉得那三瓶空了的油烟净瓶子,像三座小小的纪念碑——不是纪念苦难,是纪念一个女人在泥沼里,终于被另一个女人托了一把。 走一步看一步吧,至少现在,她的盘子里有能安心吐皮的香肠,她的房间里有能照见光的窗台。
一姑娘攒了8年32万,被亲妈偷偷拿去给弟弟付婚房首付。她没吵没闹,直接换号搬家拉
【13评论】【17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