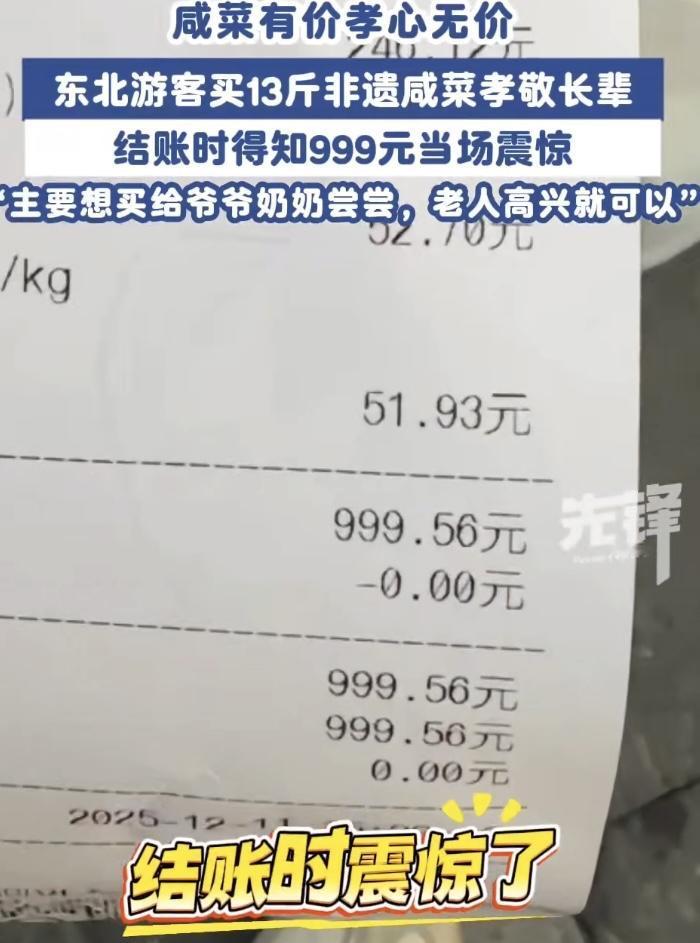堂哥瘫在30亩玉米地里时,农药瓶就对着自己, 全村人都觉得他太傻了。 但我心里清楚,压垮他的真不是那瓶农药——是堂嫂天天把“没出息”挂嘴边的念叨,是孩子打电话来,开口就问“钱够不够”,话里没一句关心的疏远,是连想喝口酒都得躲在柴房里偷偷喝的窝囊。 出事前三天,我看见他弯着腰捆玉米芯,贴身的汗衫湿得能拧出一汪水来。田埂那头,堂嫂扯着嗓子喊:“磨磨蹭蹭到天黑,看你还想不想吃饭!”他手指头抖得厉害,赶紧加快手里的活,像台生了锈的旧机器在转。那时候他眼里早就没了往日的亮堂,跟晒蔫了的玉米苗似的,蔫巴巴的。 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在他裤兜里摸到一块化了一半的水果糖,糖纸上的花纹都快磨没了——是去年闺女随手塞给他的,他硬是揣了一整年,都没舍得剥开吃。这世上哪有什么突然就想不开的?其实就是心里早被那些闲言碎语扎得千疮百孔,最后那瓶农药,不过是给这颗早就烂透的心,补上了最后一刀。 现在村里人教导自家娃时总说:“可别学老王家那样,累死累活最后一场空。”可他们都忘了,堂哥缺的从来不是力气够不够,是累趴下的时候,能有人递瓶水说句“歇会儿吧”;是家里出点事,能有人拍拍他肩膀说句“有我呢”。大伙儿说,压垮一个庄稼汉的,到底是地里的活太重,还是心里没人疼的苦太深?堂哥瘫在30亩玉米地里时,农药瓶就对着自己,全村人都觉得他太傻了。但我心里清楚,压垮他的真不是那瓶农药——是堂嫂天天把“没出息”挂嘴边的念叨,是孩子打电话来,开口就问“钱够不够”,话里没一句关心的疏远,是连想喝口酒都得躲在柴房里偷偷喝的窝囊。 出事前三天,我看见他弯着腰捆玉米芯,贴身的汗衫湿得能拧出一汪水来。田埂那头,堂嫂扯着嗓子喊:“磨磨蹭蹭到天黑,看你还想不想吃饭!”他手指头抖得厉害,赶紧加快手里的活,像台生了锈的旧机器在转。那时候他眼里早就没了往日的亮堂,跟晒蔫了的玉米苗似的,蔫巴巴的。 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是整理他东西的时候,在他裤兜里摸到一块化了一半的水果糖,糖纸上的花纹都快磨没了——是去年闺女随手塞给他的,他硬是揣了一整年,都没舍得剥开吃。这世上哪有什么突然就想不开的?其实就是心里早被那些闲言碎语扎得千疮百孔,最后那瓶农药,不过是给这颗早就烂透的心,补上了最后一刀。 现在村里人教导自家娃时总说:“可别学老王家那样,累死累活最后一场空。”可他们都忘了,堂哥缺的从来不是力气够不够,是累趴下的时候,能有人递瓶水说句“歇会儿吧”;是家里出点事,能有人拍拍他肩膀说句“有我呢”。大伙儿说,压垮一个庄稼汉的,到底是地里的活太重,还是心里没人疼的苦太深?堂哥故事 堂哥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