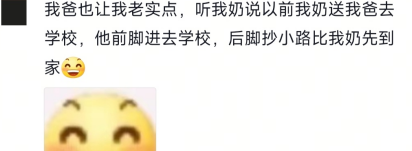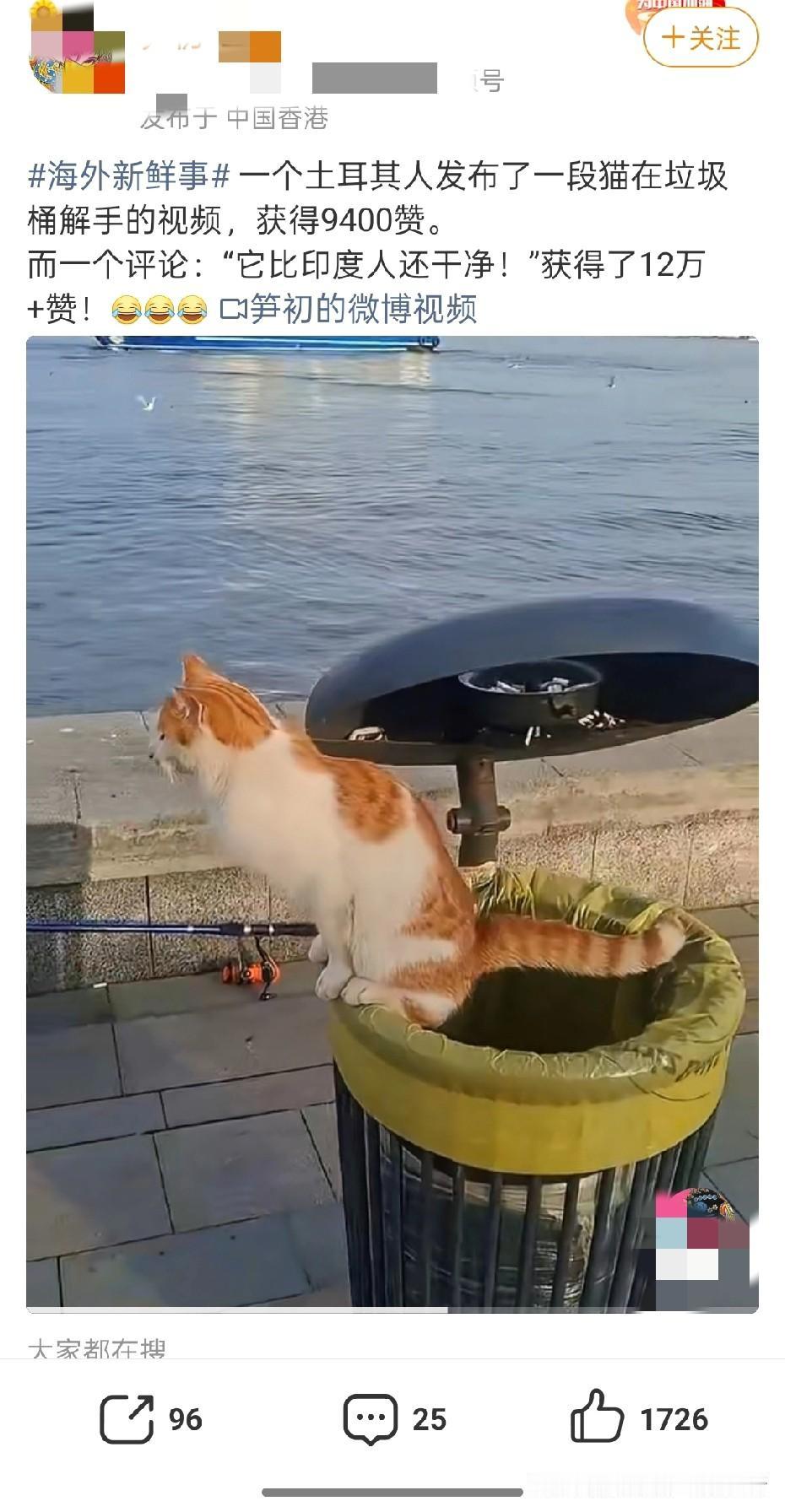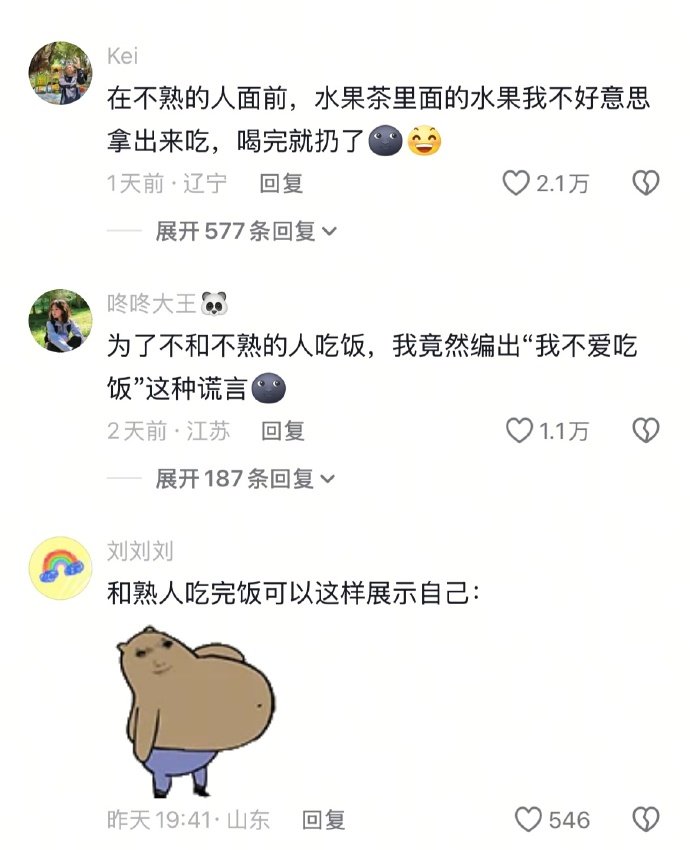我娘家的一个堂弟,一九七八年出生的,年轻的时候长得帅,人高大,十七、八岁的时候去看电影,晚上带回来一个女孩。那时候是九十年代中期,村里还没多少年轻人自由恋爱,堂弟这举动在村里炸开了锅。女孩叫玲子,家在邻县,跟着亲戚来镇上看露天电影,散场后和亲戚走散了,堂弟看她慌慌张张的,就主动说“我送你找亲戚”,结果绕了半宿没找着,天快亮时,堂弟索性把人带回了家。 我娘家有个堂弟,七八年生的,九十年代中期刚十七八,个头窜到一米八,浓眉大眼,走在村里田埂上,总有姑娘偷偷瞄他后颈的碎发。 那时候村里还兴“父母之命”,自由恋爱是稀罕事,连媒人说亲都得托三姑六婆递话。堂弟偏不,偏在那年秋天的露天电影散场后,把一个陌生女孩领回了家。 女孩叫玲子,邻县来的,跟着表姑来镇上看《少林寺》。散场时人挤人,她手里攥着半袋没吃完的炒瓜子,一回头,表姑早没影了。九月的夜风裹着玉米秆的甜香,她站在晒谷场边,路灯昏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株没扎稳根的麦苗。 堂弟刚跟伙伴赌赢了一包烟,正叼着烟蒂往家走,撞见她蹲在石碾子上抹眼泪。“咋了?”他把烟蒂摁灭在鞋底,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后来他说,那刻怕吓着她,连呼吸都放轻了。 “我找不着表姑了……”玲子抬头,眼里还汪着泪,睫毛上沾着点灰,倒显得眼睛更亮。堂弟挠挠头,“我送你找去”,话一出口就后悔了——他哪知道她表姑住哪? 两人揣着半袋瓜子,从镇东头走到镇西头。供销社早关了门,只有守夜人的马灯在墙根晃;卫生院门口的狗吠了两声,又夹着尾巴缩回去。玲子的帆布鞋磨得后跟发红,堂弟索性蹲下来,“上来,我背你”,她犹豫了一下,轻轻趴在他背上,温热的呼吸喷在他后颈,比烟蒂烫多了。 绕到后半夜,月亮都快落了,玲子突然说:“要不……去你家歇歇吧?”堂弟心里咯噔一下——他爹娘早睡了,堂屋的门从里面插着,咋进去?可回头看玲子眼皮打架的样子,还是咬咬牙:“走。” 他翻墙进院,摸黑拔了门闩,把玲子领进东厢房。灶台上还温着红薯粥,他盛了碗递给她,她小口喝着,眼泪又掉下来,砸在粗瓷碗沿上,“我以为……今晚要睡麦秸垛了。” 天快亮时,婶子起夜,撞见东厢房亮着灯,推门一看,吓得手里的尿盆“哐当”掉地上——自家儿子和个陌生姑娘并排坐着,地上堆着瓜子皮。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上午飞遍全村。三奶奶拄着拐杖来串门,“你家小子胆忒大,也不怕是人贩子?”二伯蹲在门槛上抽旱烟,“这要是传出去,玲子还咋嫁人?”堂弟蹲在院角,不吭声,只把玲子的帆布鞋刷得雪白,晾在篱笆上。 后来呢?玲子在村里住了三天,表姑才找过来,看见玲子跟堂弟在晒谷场晒玉米,两人并排翻着玉米堆,影子叠在一起,倒像是住了一辈子的样子。表姑要带玲子走,玲子攥着堂弟的衣角不松,“我不走”,堂弟也梗着脖子,“她留下”。 谁能想到,那场散了场的电影,会让两个陌生人的路,在九十年代的乡村小路上,绕成了一辈子的牵绊?村里人说堂弟“愣”,说玲子“野”,可谁也没看见——那晚堂弟背她时,悄悄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她身下;玲子后来总跟我婶子念叨,“他后背汗湿的印子,像张摊开的地图,我跟着走,就不怕迷路了。” 如今堂弟和玲子的儿子都上大学了,院角那棵老槐树还在,每年春天开得满枝白花。有次我问玲子,后悔那天跟个陌生人回家吗?她正择菜,手顿了顿,抬头看堂弟在门口修自行车,阳光落在他鬓角的白霜上,“后悔啥?要不是他绕了半宿没找着路,我哪能遇见个把我当宝贝疼的人?” 风从厨房窗户吹进来,带着槐花香,像极了那年秋天,露天电影散场后,裹着玉米秆甜香的夜风——有些路看似绕远了,却偏偏把人引到了该去的地方。
我堂哥在巴基斯坦打工那会儿,稀里糊涂就跟当地一个姑娘好上了。哪知道姑娘全家知道后
【5评论】【1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