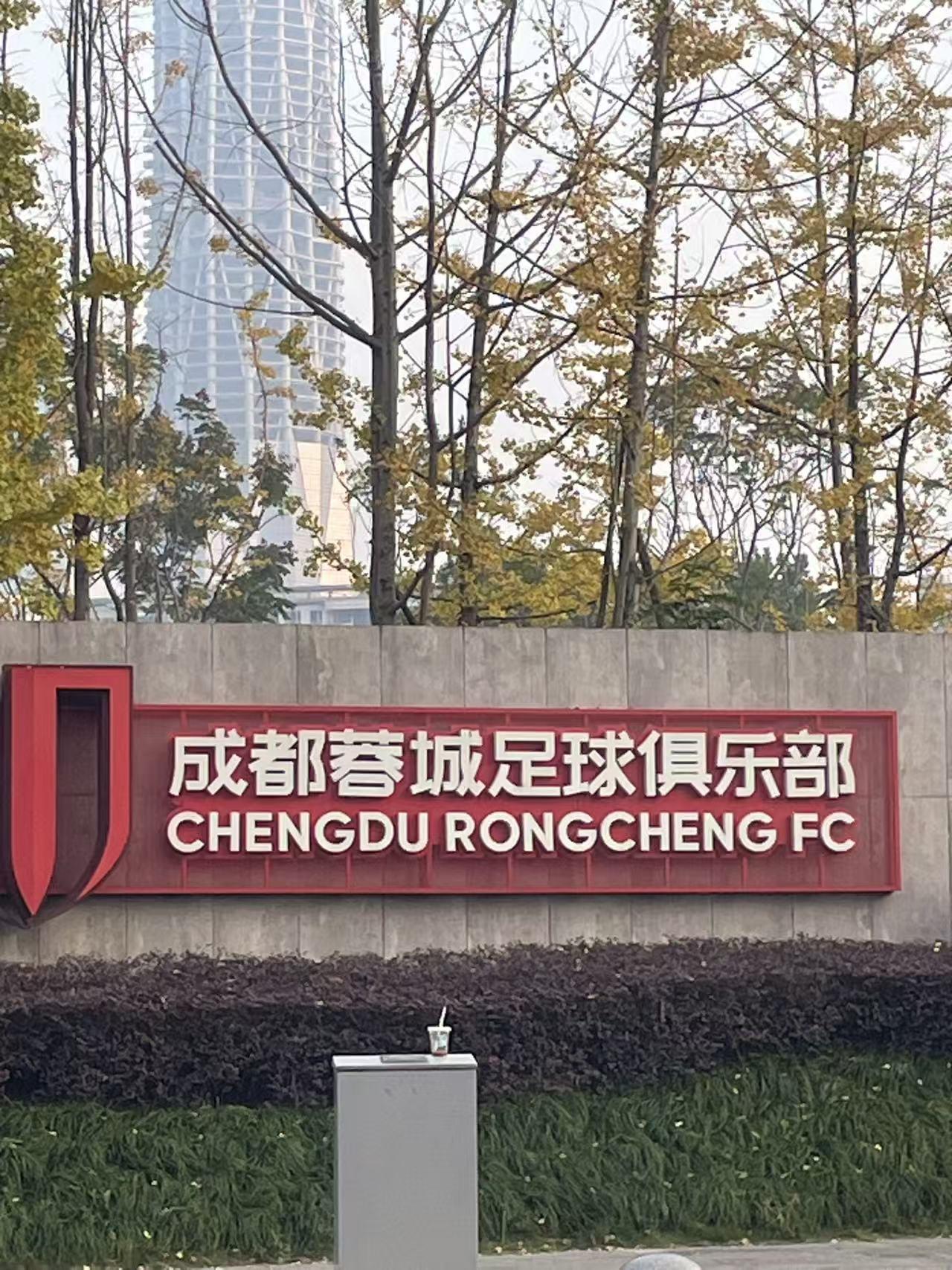她下班买菜回家,看见弟媳在单元门口站着,看见她后笑着说:“嫂子,你可回来了。”她看了弟媳一眼,说:“哦,找我有什么事,我一会儿还要去接月月,有事就快说。”弟媳搓着手往楼道里缩了缩,初冬的风卷着碎雪沫子打在人脸上生疼。 五点半,天擦黑的时候,她拎着菜走到三单元门口。 塑料袋里的青椒沾着泥,萝卜缨子还绿着,是刚从菜市场抢的新鲜货——接月月前,她总爱绕去老李家摊位,今天却被风催得步子急。 路灯忽闪了两下,才看清阴影里站着个人。 “嫂子,你可回来了。”弟媳的声音裹着风飘过来,带点怯生生的笑。 她抬头,撞上对方冻得发红的鼻尖,还有那件拉链早坏了的旧羽绒服,风正顺着敞开的领口往里灌。 “哦。”她应了声,低头看手腕上的电子表:5:32,月月放学该等急了。“找我有事?我一会儿还得去接孩子,有事就快说。” 弟媳往后缩了缩,脚后跟差点踩到楼道台阶上,两只手在身前使劲搓,指关节红得像浸过冷水的樱桃。 “我……”她张了张嘴,风突然卷着碎雪沫子扑过来,把后半句噎了回去。 她忽然想起去年冬天,自己发烧到39度,是弟媳踩着雪去学校接的月月。 孩子回来时,裹在弟媳那件灰扑扑的棉袄里,小脸通红,而弟媳半边肩膀全湿了,头发上的雪化成水,顺着发梢滴在楼道地砖上,一串小小的水印。 那时候她怎么说的?好像是“谢了啊,改天请你吃饭”,然后就忙着给月月煮姜汤,连杯热水都没给弟媳倒。 “到底啥事?”她把手里的菜往臂弯里紧了紧,青椒硌得胳膊有点疼。 弟媳终于抬起头,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妈今天打电话,说老家屋顶漏了,一下雨就往下滴水,爸想找人修,手里……手里还差三百块。”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被风吹散。 她愣了愣。三百块。 上个月她给月月报钢琴班,眼睛都没眨就交了三千;昨天同事聚餐,一顿饭吃了五百八。 而弟媳在这冷风里站了多久?看她羽绒服上的雪沫子,至少半小时了吧——从她下班时间推算,弟媳四点半就该来了。 “进楼道说吧,风大。”她转身往楼道走,没回头。 弟媳跟在后面,脚步轻得像怕踩碎地上的影子。 人是不是都这样,对越亲的人,越容易把耐心藏起来?好像笃定对方永远不会走,就敢把最硬的刺亮给人家看。 她总说自己忙,忙着上班忙着接孩子,忙着把日子过成陀螺,却忘了停下听人把话说完;弟媳呢,越怕给人添麻烦,越把话往肚子里咽,结果两人之间的那层冰,倒像是她亲手一勺一勺冻出来的。 打开家门,她把菜放在玄关柜上,转身去厨房倒水。 玻璃杯底碰到桌面时,她听见弟媳在门口小声说:“嫂子,要不我还是……” “喝了水再说。”她把水杯递过去,指尖碰到弟媳的手,凉得像块冰。 弟媳接过杯子,热气模糊了她的眼镜片,她赶紧抬手去擦,却把水洒在了手背上,烫得“嘶”了一声。 她忽然笑了,从钱包里抽出三百块,塞进弟媳手里:“拿着,跟我还客气什么。” 弟媳的手颤了颤,钱被捏得皱巴巴的,像片被揉过的树叶。 “嫂子,我……” “行了,”她打断她,把自己的围巾摘下来,往弟媳脖子上缠了两圈,“快回去吧,一会儿你家小宝该等你做饭了。” 弟媳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三次。 楼道灯在她身后明明灭灭,碎雪沫子还在飘,落在围巾绒毛上,很快化成了小水珠,像谁没忍住的眼泪。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空荡荡的脖子,忽然觉得,刚才那点不耐烦,比这初冬的风还冷。 其实日子哪有那么赶?慢一步,等一句,给杯热水的功夫,就能把冻僵的关系捂热乎了。 就像现在,她拿起手机给月月班主任发消息:“老师您好,我晚十分钟到,麻烦您帮忙照看一下孩子。” 发完消息,她把弟媳落下的那只毛线手套捡起来,揣进了兜里——明天上班路上,给她送去。
她下班买菜回家,看见弟媳在单元门口站着,看见她后笑着说:“嫂子,你可回来了。”她
勇敢的风铃说史
2025-12-17 14:20:45
0
阅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