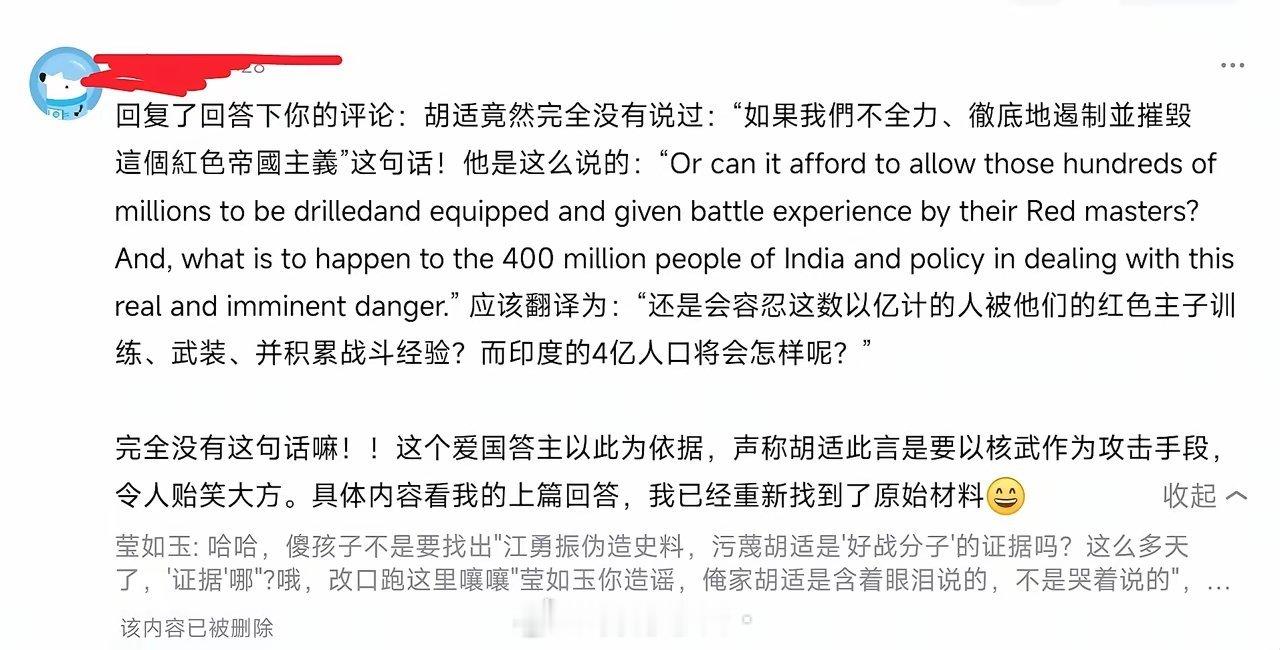晚清时期,婉容把太监孙耀庭叫进闺房,命令他伺候自己冲澡,谁知,当她解开衣衫,孙耀庭突然低头说:“奴才肚子痛,无法伺候您了!” 1990年,北京兴隆寺的枯树下,88岁的孙耀庭摩挲着一块旧得泛黄的绣兰手帕。老人的手指关节粗大,那是晚年捡废品留下的痕迹,但触碰这块丝帕时,他的动作轻柔得像是在触摸一段易碎的时光。 这块手帕的主人,是早已化作白骨的末代皇后婉容。在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太监的记忆深处,那堵红墙内的日子并非全是史书里冰冷的宫斗,更多的是两个被时代困住的年轻人,在那座早已腐朽的牢笼里试图保留的一丝“人味”。 时光回溯到1923年,那时的储秀宫里,空气总是混浊而暧昧。对于出身显赫的婉容来说,这世上的男人只分两种:皇上和其他。至于太监,那是会喘气的物件,跟澡盆、胰子没区别。 从小被人伺候惯了的她,甚至不知道洗澡也是需要回避的私密事。当她极其自然地准备入浴,全然不顾旁边站着刚分来的小太监时,21岁的孙耀庭却慌了。 他不像那些从小入宫、早就在规矩里麻木的老太监。他是15岁才挨的那一刀,也就是现在读初中的年纪,也是懂人事、知羞耻的少年郎。 身体虽然残缺了,心里那根作为男人的刺还在。面对那个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少女赤裸的身体,巨大的羞耻感压过了皇权。他猛地低下头,甚至不敢睁眼,憋出一句:“奴才肚子痛。” 这句拙劣的谎言,是他作为一个并未完全泯灭人性的灵魂,最后的遮羞布。 婉容笑了,笑得清脆,那是富家小姐对“物件”突然有了情绪感到新奇。她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些愚笨的奴才,为了掩盖身上所谓的气味,即使是冬天也要五天洗一次澡,把自己刷得发红,甚至还要偷偷抹雪花膏。在一个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孙耀庭偏要干干净净地把自己当个人看。 他发现这个白天不可一世的皇后,竟然怕黑。于是每逢守夜,他总会将廊下的灯笼挑得比平日更高、更亮些。 这一点小心思,没有逃过婉容的眼睛。那块绣着兰花的手帕,便是在某个清晨被随手赏下来的,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句并不像主子对奴才说的话:“地上凉,往后不用跪太久。” 这大概是深宫里极为罕见的温情时刻:一个用光亮驱散主子恐惧的奴才,和一个许诺奴才少跪一会的皇后。 但时代的洪流从来不给人准备的机会。1924年秋,冯玉祥的军队并没有给这座皇宫留太多体面。在那个慌乱的深秋夜晚,婉容不再是那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娇小姐。 在孙耀庭帮她收拾细软时,她异常严肃地塞给他一包碎银,并留下一句话:如果外面的兵要钱,就给他们,保命要紧。 分别那一刻,兵荒马乱。婉容上了车,透过车窗回头的一瞥,成了两人此生的诀别。她留给孙耀庭一本诗集,扉页上那句手写的“愿君安”,成了孙耀庭后半生颠沛流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 出了宫墙,世界变得更加残酷。曾经拿拂尘、端茶碗的手,根本握不住农家的锄头。孙耀庭回了老家,却因为不会干农活被乡邻嘲笑,甚至连顽童都敢追着他扔石头骂“阉人”。他只能在破庙栖身,靠给别人放牛换口残羹冷炙。 当严冬的寒风灌进骨缝,那一包碎银成了他没冻死饿死的底气;当高烧不退几乎要命丧黄泉时,是同住在寺庙里的落魄老太监们凑钱买草药救了他,而那块贴身藏着的手帕,在无数个发热的噩梦里,替他擦去了冷汗和泪水。 曾经的主子和奴才,命运走向了两极。婉容跟着溥仪辗转,最终在伪满洲国的虚幻美梦中破碎,染上烟瘾,精神崩溃,40岁便凄惨地病逝于延吉,死后据说只裹了一卷草席。 而孙耀庭在经历了捡废品、乞讨的极度困窘后,反而在新中国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政府每月发放的16元生活费,让他终于不必再为一口饭下跪;后来管理的寺庙出纳工作,让他在这个人间重新找回了尊严。 1946年,当婉容离世的消息传来,孙耀庭把自己关在屋里。他没有大哭,只是对着东北方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那一刻,他拜的或许不是皇后,而是那个曾塞给他一包救命钱、叮嘱他“保命要紧”的善良女子。 91岁那年,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的孙耀庭,颤巍巍地翻开了那本保存了近70年的诗集。在扉页那句已经褪色的“愿君安”旁边,他用毛笔歪歪扭扭地补上了五个字:“君安否,我安。” 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主仆对话,终于画上了句号。他做到了她当年的期许,活了下来,活得像个人。 1996年,这位中国最后的太监走完了他94岁的人生旅程。遵照遗愿,那块绣兰手帕和题字的诗集,作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见证,随他一同化为灰烬。 对于孙耀庭而言,紫禁城是一场漫长的噩梦,但这手帕和诗集,是噩梦醒来后,手里攥着的唯一一颗糖。它们证明了,即便是在最压抑人性的体制里,两颗微小的心灵,也曾努力温暖过彼此。 主要信源:(中国历史网——孙耀庭:中国最后一名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