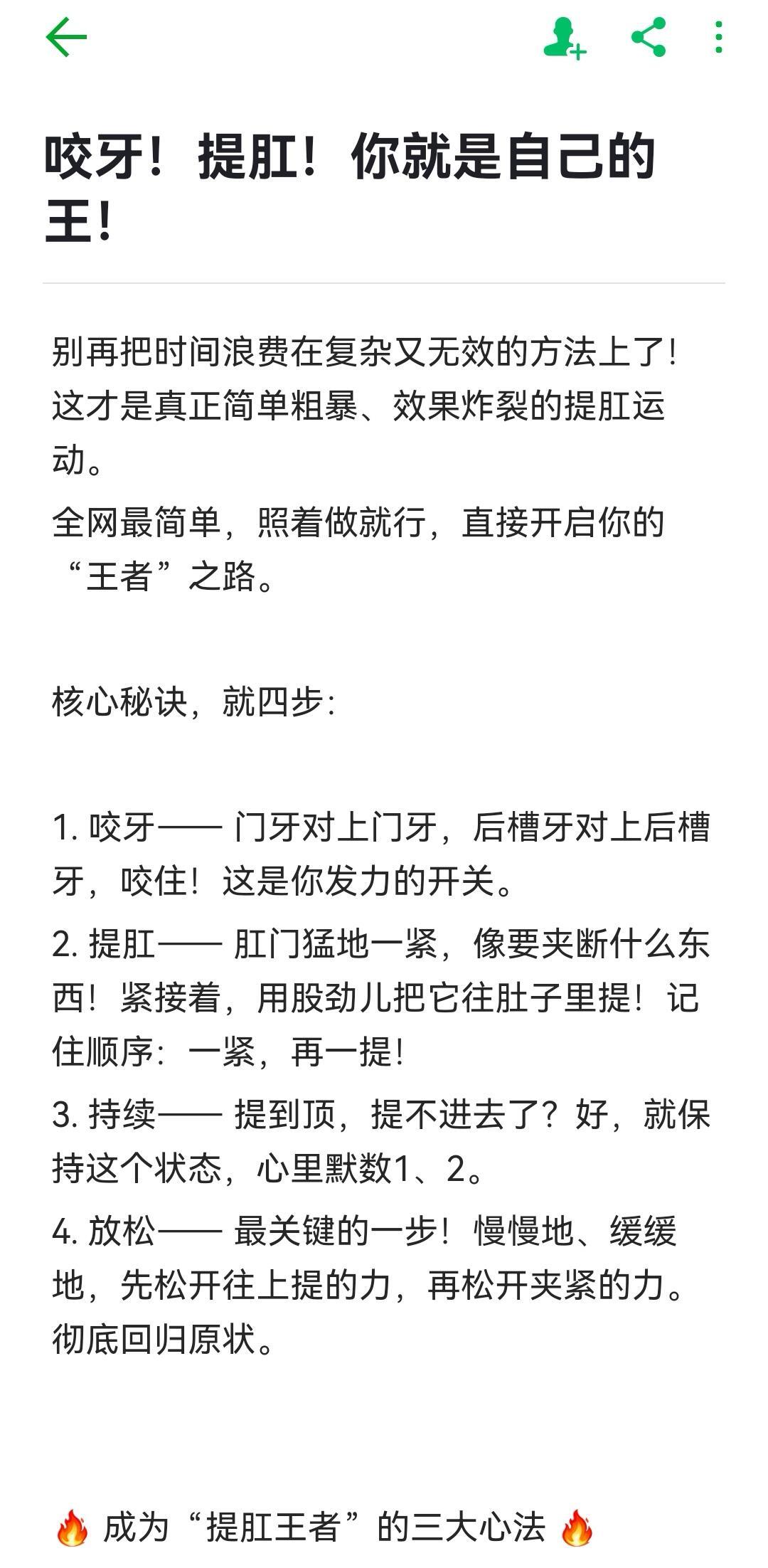我舍不得删的,是那双眼睛。 早年间,外公的眼睛是锐利的鹰眼。墨线轻轻一弹,笔直的印记便在木料上苏醒,分毫不差。刨花从刨子下翻卷而出,像舒展的浪,空气里满是松木和樟木清冽的香气。那时他的手,是年轻的山脉,关节突出,力量在皮肤下奔流,能稳稳握住沉重的斧凿,也能捏着细砂纸,将一块顽木打磨出绸缎的光泽。他看木头的眼神,是君王在检阅他的疆土,笃定,威严,充满创造的激情。 岁月是另一个技艺高超的匠人,它不用斧凿,却重新塑造了这双手。我照片里的那双手,皮肤薄如陈年的宣纸,包裹着嶙峋的骨节与蜿蜒的青色脉络。那些被无数次木屑嵌入又洗净的纹路,像老树的年轮,深不见底。一道新鲜的伤口横在虎口,渗着细微的血珠,是最后一次尝试时,不听使唤的凿子留给他的纪念。指甲缝里,洗不净的褐色木尘,已成为身体最后的徽章。 可最动人心魄的,是那双手的姿态。它们不再紧握,而是松弛地、略带颤抖地,虚虚地拢着那块未成形的木料。指尖极轻地触碰着木纹的走向,像盲人在阅读盲文,像乐师在调试琴弦。那不是创造者的手,而是告别者的手。他在用触觉,重温一生与木头对话的语言。力量从肌肉中退潮了,但理解与柔情,却在此刻涨至满溢。这双手曾驯服过无数倔强的木材,如今,它正温柔地放走最后一位“未完成”。 我忽然懂得,我们舍不得删的照片,往往与“技艺”或“成就”无关。它截取的,是一个生命与世界最终的和解姿态。那双曾劈削、雕刻、建造的手,在力的尽头,学会了抚摸。外公没有做出那个凳子,但他完成了一件更伟大的作品——他为自己的热爱,举行了一场寂静而庄重的告别式。 照片静静躺在手机里。我舍不得删的,是那双在暮色中,从“驾驭”缓缓渡向“懂得”的手。它让我看见,当生命的力气像潮水般退去,留在沙滩上的,是最温柔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