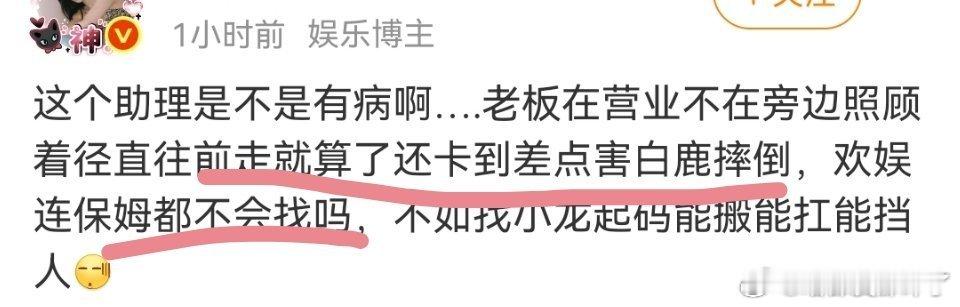清代某县忽然出现一个淫贼,由于都在夜间作案,而且带着面罩。因此县衙的捕快追查许久却毫无头绪!一时间风声鹤唳,女子都不敢独自出门。只是苦了那几个受辱的女子,有的忍受不了世俗闲语,直接一根白绫了断了性命。 二十岁的荔姐攥着刚收的几枚铜板,指尖还沾着瓜藤的黏液。她和丈夫张三在县城南门外支着瓜摊,青绿色的西瓜堆得像小山,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 熟人喘着气跑来时,张三正用草绳捆最后两个裂了纹的瓜。“荔姐,快回!你娘中风倒了!”话音未落,荔姐已把铜板塞进张三手里,转身往城外小路跑——那条路平时只有樵夫和坟户走,此刻暮色像墨汁般泼下来,树影张牙舞爪。 身后的脚步声像擂鼓,一声比一声近。荔姐头皮发麻,前几日王屠户家的小女儿就是在这条路上出事的,哭喊声在巷子里飘了三天,最后只剩梁上悬着的白绫轻轻晃。 她突然瞥见路边那座塌了半边的荒坟,坟前那棵歪脖子槐树上还挂着去年的纸钱。怀里的香粉盒“哐当”撞在腰间——早上出门时为讨吉利,她顺手抓了胭脂铺买的茉莉粉。 脚步追到坟前时,荔姐猛地转身。她扯散发髻,让头发垂到腰际,又抓了一大把香粉往脸上抹,惨白的粉末混着汗水流进脖子,凉得她打了个颤。衣服被她扯松挂在槐树枝上,风一吹,像飘在半空的鬼影。 “姑娘,跑什么?”无赖的声音黏糊糊的,带着酒气。他白天就在瓜摊前打转,眼睛直勾勾盯着荔姐挽起的袖口,此刻手里还攥着块脏帕子。 荔姐弯腰捡起半截断裂的墓碑,压低嗓子,声音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你前夜摸进王家时,可看清我脸上这道疤?”她故意把脸往月光下凑,香粉簌簌往下掉,倒真像有道狰狞的印记。 无赖手里的帕子“啪嗒”掉在地上。他后退两步,脚腕被坟前的石供桌绊倒,整个人摔在乱草里。“鬼……鬼啊!”他喉咙里发出破锣似的响,裤腿很快湿了一片,腥臭气混着泥土味飘过来。 荔姐没回头,一口气跑回家时,天已全黑。灶台上的油灯晃了晃,映着母亲蜡黄的脸,她才发现手心的香粉盒边角已被攥得变形。 第二天清晨,卖豆腐的老汉挑着担子走过桥头,听见几个妇人在说:“昨晚西头坟地闹鬼了!有个男人光着膀子躺在那儿,疯疯癫癫喊‘我是淫贼’,裤裆湿得像尿了床!” 没人知道那是荔姐的手笔,但“女鬼索命”的传言像长了翅膀。有婆子说看见白衣影子在坟头飘,有货郎说听见半夜有人哭着认错——“我不该扒李家媳妇的衣裳”“张家姑娘是我推下河的”。 那时的女子出门,怀里总要揣着两样东西:一是《女诫》的小册子,二是剪刀或毒药。《大清律例》写着“强奸绞刑,未遂三年”,可县衙的捕快总在酒肆里推杯换盏,士绅家的子弟就算被抓,也总有“年少无知”的理由开脱。更糟的是街坊的唾沫——受辱的女子走在路上,背后的窃窃私语比刀子还利。 荔姐不是第一个反抗的。光绪六年山东有个曹氏,半夜被土匪摸进家,她抄起剪刀就扎,土匪捂着流血的胳膊跑了,官府最后判了“正当防卫”。可曹氏回娘家时,嫂子还是把她用过的碗筷单独收在灶角。 大多数时候,女子的反抗是无声的——是井台上那桶沉得提不动的水,是油灯下缝补到天亮的衣裳,是被问到“那晚到底怎样”时,突然红了的眼眶。 荔姐的香粉盒后来挂在了村口的老槐树上。里面的茉莉粉早被风吹散了,盒子却被磨得锃亮。有小媳妇走夜路,会对着盒子拜一拜,再往脸上抹点灶灰——她们学不会扮鬼,却记住了那个往脸上拍香粉的姑娘。 再后来,县衙贴出告示说“淫贼已擒”,可没人见过犯人。倒是南门外的瓜摊前,总有人多给几个铜板,张三推辞时,对方就笑:“给荔姐的,买盒新香粉。” 那些曾经紧闭的院门,渐渐敢在傍晚留条缝;巷子里的碎语少了,多了妇人结伴挑水的笑声。 人们叫她“白衣娘”,说她是坟地里爬出来的菩萨。只有荔姐知道,那晚她抹的不是香灰,是自己的汗;吓退的不是淫贼,是压在女子心头的那座坟。 风穿过槐树叶,沙沙响。香粉盒在枝头轻轻晃,像在说:天再黑,总有人敢点起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