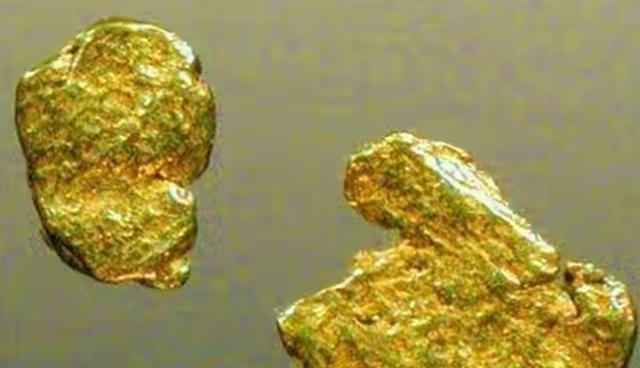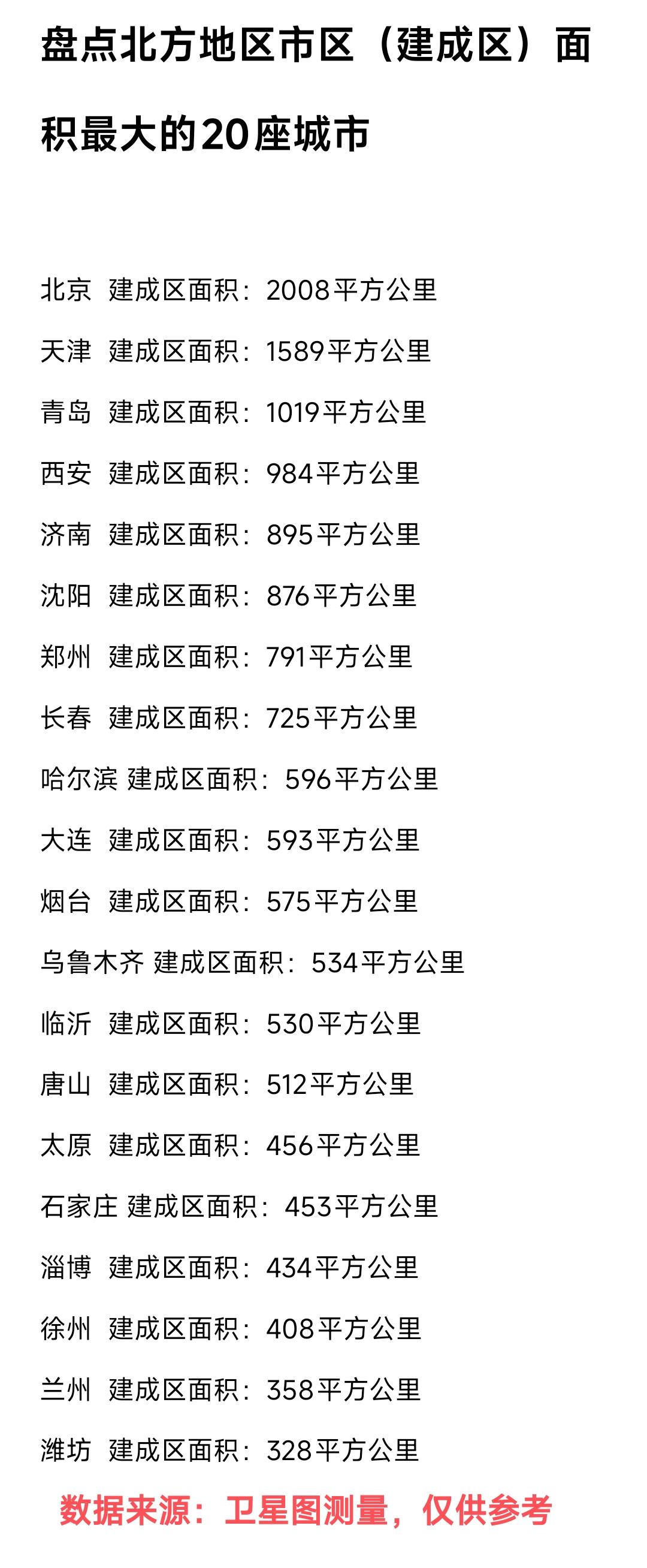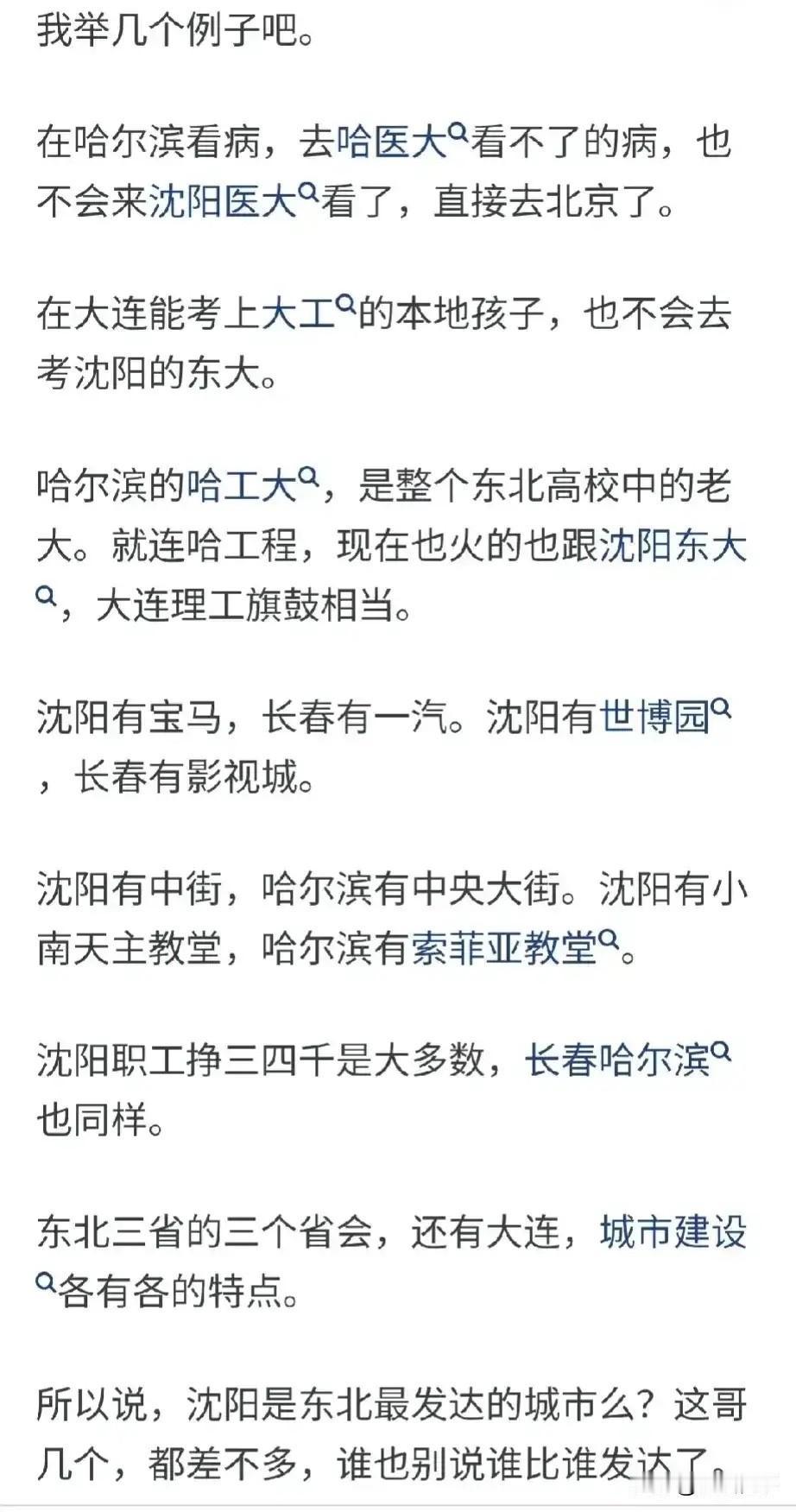1980年,沈阳妇女黄淑珍带着3斤黄金来银行兑换。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来她拿来的是纯度很高的工业黄金,立即就引起了警惕。 1980年的沈阳,空气里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严谨与质朴。就在这看似平常的日子里,一位名叫黄淑珍的家庭主妇走进了银行的营业大厅。她的手中紧紧攥着一个有些份量的布包,脸上挂着一种极力掩饰却又欲盖弥弥彰的忐忑。 在那个人均工资并不高的年代,她怀揣的是整整三斤黄金。但这并非寻常人家传下来的金镯子或金锁片,当布包在柜台的一角被解开时,连见多识广的银行柜员呼吸都顿了一拍。 展现在眼前的是几块形态并不规则的“金疙瘩”,它们边缘有着粗糙的切割痕迹,没有商业铭牌,没有制造局的戳记,但那种刺眼的金黄色泽和惊人的密度,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它的纯度——这是高达99.9%的工业级高纯金。 柜台后的营业员是个精明人,那一瞬间,她脑海里的警铃大作,这东西不是“民脂民膏”,而是实打实的“国家命脉”。 虽然内心惊涛骇浪,但她的职业素养让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她并没有当场拒绝,反而做出一副认真评估的样子,拿出计算器敲敲打打,最后给出了一个在那时堪称天文数字的估价——两万三千多元。 “大姐,这钱数额太大,拿现金不安全,不如存个折子,以后随用随取?”营业员的语气温和又体贴。 这一番话,像是定心丸一样安抚了黄淑珍紧绷的神经,她原以为会被盘问来源,没想到手续如此顺利,眼前的利益让她瞬间放松了警惕,当即点头应允。 殊不知,就在她低头填单子的空档,营业员的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身旁的同事,两人之间无需多言,一个眼神交汇,同事便借口去后库拿单据,转身就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 不到二十分钟,两名穿着便衣的民警就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黄淑珍的身后。 “有些情况需要跟你核实一下。”当这句话响起时,黄淑珍手中刚拿起的笔“啪”地一声摔在桌面上,刚才还畅想着两万多元巨款带来的新生活,瞬间变成了苍白的惊恐。她试图张嘴解释,但面对民警那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所有的谎言都被堵在了嗓子眼。 在审讯室里,面对严肃的询问,黄淑珍死守着沉默足足半个小时,那是她内心最后的挣扎,但随着心理防线的崩溃,这三斤黄金背后的“硕鼠”终于浮出水面——那是她的丈夫,张国栋。 张国栋并非什么江洋大盗,而是沈阳一家大型机械厂的一线技术员,他的工作就是与这些贵重金属打交道,负责加工那些精密部件。 按理说,拥有这样的技术岗位在当时已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浪潮下,物质欲望开始悄然生长,家里紧巴巴的日子、孩子未来的学费、想换套新房的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最终吞噬了职业操守。 早在1979年下半年,张国栋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车间管理的疏漏,那时的制度虽有,但执行层面却有不少“空子”。比如黄金原料的领用登记流于形式,加工后剩下的金粉、边角料,在回收环节也没有严格的称重对账。 这种监管的真空,成了张国栋眼中的“机会”。 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搬运”计划。每天下班,他利用随身携带的饭盒底部,甚至是衣服特意缝制的夹层,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点地将打磨下来的金粉和细碎边角料带出工厂,在张国栋看来,这些只是“废料”,国家家大业大或许不在乎这这一点点损耗。 日积月累,这些不起眼的“粉末”被他在家中私自熔炼,最终变成了这三块沉甸甸的金砖。夫妻俩在灯下看着这些金光闪闪的东西,想的尽是未来的好日子,却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些金属原本的归属——它们是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国有资产。 这对夫妻的侥幸心理,在银行柜台专业人员的识别能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1980年,国家对于黄金,特别是工业用战略黄金的管控有着极为明确的红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占有、倒卖、处置,违者必究。 这起案件在当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果也是惨痛的。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含糊:张国栋因盗窃国有资产数额巨大,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黄淑珍作为共犯,获刑5年。那一笔本以为能改变命运的“两万三千元”,最终换来的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这个布包里的三斤黄金,不仅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也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当时许多正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企业单位。 案件发生后,张国栋所在的机械厂乃至当地的多个相关单位,迅速开展了亡羊补牢式的整改。松散的领料制度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双人复核、精确到毫克的称重对账,确保国家的战略资源不再有流失的缝隙。 如今回头再看这起1980年的旧案,那闪着幽光的工业黄金,实际上映射出的是那个特定年代里,个人私欲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剧烈碰撞。它警示着后来人:无论身处什么时代,面对公有的资源,守住底线不仅仅是职业要求,更是为人立世的根本。用非分的手段去触碰红线,得到的永远不会是财富,只能是代价。 信源:1.5公斤黄金抵押品被扣14年,沈阳一寄卖行申请国家赔偿——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