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教授令人深思的话: “战争结束后,政客们握手言和,瓜分地盘;将军们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商们抢夺资源,经商发财;唯独只有穷人,在掩埋孩子的尸骨。战争,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杀死另一个农民的儿子,他们背井离乡,以身犯险,来到陌生的地方,献出生命。不是别人和他有仇,而是有人告诉他们,那是你的仇人,战争的本质,不过是资源的重新分配。但是,最大的悲哀却是,太平本是英雄创,却不见英雄享太平。” 村口的河水,往年这时候该是浑浊的、带着泥土腥气的黄。如今却清得发亮,静悄悄地从两座新垒的土坟边绕过。 老李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握着半片没补完的渔网。保长带着人挨家挨户拍门,说北边吃紧,要人。 他大儿子蹲在墙角,把最后一口旱烟抽完,烟灰磕在鞋帮上,站起身:“我去。” 渔网那个破洞,再也没补上。 村东头的赵老倌,也在同一天送走了独子。两个年轻人在祠堂前磕了头,领了薄得像纸的灰布军装,一前一后上了那辆哐当作响的卡车。 他们没说话,只是赵家小子扭头时,看见老李家老大正盯着自己脚上那双露趾的布鞋,眼神愣愣的。 仗打了三年。消息有时像风,有时像石头。风过无痕,石头沉底。 老李学会从村长脸色猜战事,眉头紧锁,就是又败了;稍有舒展,便是僵持。 至于“大捷”的消息,总是由骑着马的传令兵带来,声音洪亮地念完,村庄依旧死寂。那捷报上的地名,老李一个也没听过。 河水第五次结冰又化开的时候,一辆吉普车扬起尘土开进了村。下来几个穿呢子大衣的人,在晒谷场上说了很久的话。 老李远远站着,只听见“光复”、“胜利”、几个词在风里打旋。有人开始发东西,一块硬邦邦的肥皂,一小包白砂糖。 老李领了,糖纸在手里窸窣响,甜味还没闻到,胃里先涌上一股酸水。 傍晚,赵老倌佝偻着背过来,手里攥着个布包。 打开,是一枚生锈的勋章,一张模糊的阵亡通知书,还有一块没吃完、已经板结得像石头的压缩饼干。 “一起运回来的,”赵老倌声音干涩,“说他们……一起没的。” 老李接过那勋章,边缘硌手。他想起大儿子走那天穿的草鞋,大拇指的地方快要磨穿了。而眼前这金属的冰凉,据说代表光荣。 晒谷场上很快搭起了戏台,咿咿呀呀唱起《龙凤呈祥》。穿呢子大衣的人不见了,换了些面色红润的商人,围着村长商量收购后山木材的事。 孩子们在崭新的、印着“戡乱救国”的标语牌下追逐嬉戏。 老李和赵老倌在河边埋下了那枚勋章和那块硬饼干。没有立碑,只是各插了一根柳枝。 河水依旧静静地流,清澈见底,照出两个老人佝偻的、沉默的倒影,也照出远处戏台上晃动的、鲜艳的光影。 《庄子》有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发动与结束战争的人,用普通士兵的尸骨作为筹码,完成了一次资源的“合法”再分配。而失去孩子的穷人,连悲伤都成了沉默的哽咽。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在战争这台庞大的机器面前,普通士兵便是那“刍狗”。 他们被崇高的名词召唤,被简化为地图上的箭头与统计表里的数字。 他们的爱恨、恐惧与乡愁,在“大局”面前轻如草芥。这不仅是战争的残酷,更是权力对人性的漠视。 曾国藩深谙权谋,其言“结盟一事,未可轻诺”,道破了所有联盟的利益本质。 将军与政客们达成了新的平衡,而牺牲者则成了过时的筹码,被扫入历史的角落。 所以,世人最大清醒,不是歌颂牺牲,而是竭力避免让任何人的儿子,再为了少数人的棋盘,去杀死另一个老父亲的儿子。 你觉得发起仇恨和战争的人可恨吗?



![负亲不负国,将军大义[赞]](http://image.uczzd.cn/1018057069059243486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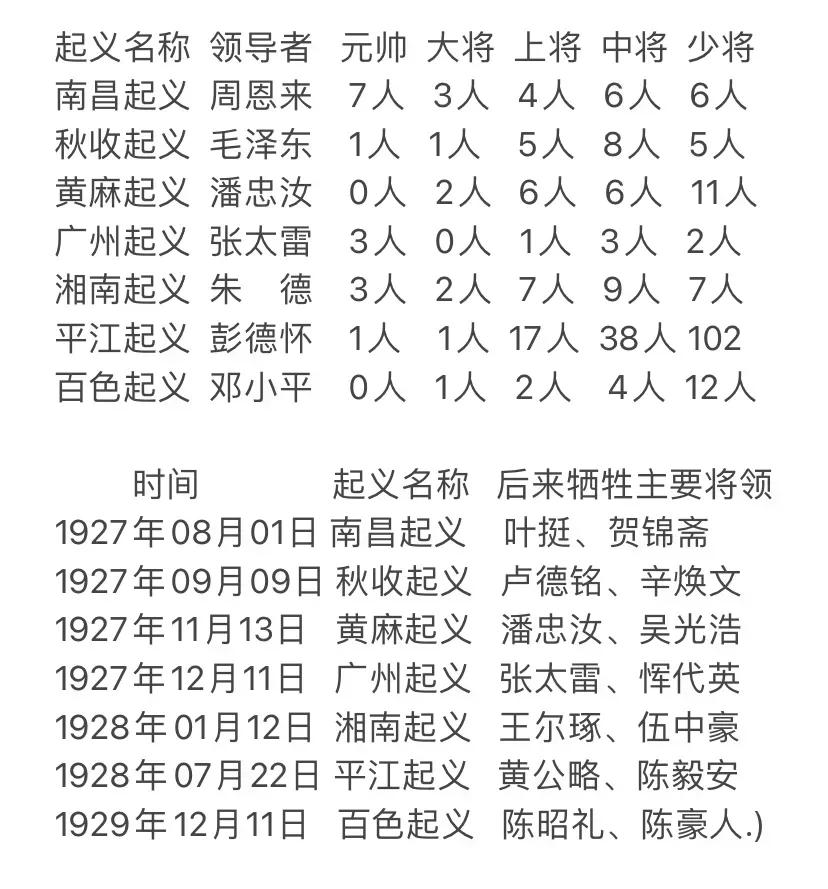



Life
这个薇薇有问题,希望彻查一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