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有钱有势,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后来他又发了消息,我也装作没看见,只因为前年我父亲去世,他竟然一个关心的电话都没有。下午四点多,我正收拾厨房,听见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不是按门铃,是用手砸的那种,力道大得像是要把门拆了。 厨房飘着洗洁精的柠檬香,我正把最后一只碗放进消毒柜,手机在客厅第三次震动起来。 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让我手指一顿——大伯。 三个未接来电,两条未读消息,我盯着水流顺着水槽蜿蜒而下,像极了前年父亲走时,我怎么也流不干的眼泪。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电话不接,消息不回,仿佛我们家从未有过父亲这个兄弟。 下午四点二十八分,防盗门突然发出"哐哐"的巨响,不是门铃的叮咚,是手掌拍在铁皮上的闷响,一声比一声急,震得门框都在颤。 我握着擦碗布的手猛地收紧,指节泛白——这个点,会是谁? 透过猫眼望去,大伯穿着挺括的黑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那双总是端着架子的手,此刻正焦躁地砸着门,像是要把过去两年的空白都砸进这扇门里。 门开的瞬间,他带着一身寒气挤进来,名贵皮鞋在地板上蹭出两道印子:"你聋了?电话为什么不接!" 我后退半步,闻到他身上熟悉的雪茄味,突然想起父亲生前总说:"你大伯啊,心早就被钱熏硬了。" "有事吗?"我把擦碗布搭在肩上,声音平得像块木板。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愣了一下才从公文包掏出个红本本:"你堂哥要结婚,下月初,这是请柬。" 红本本烫金的"囍"字刺得我眼睛疼,我想起父亲的葬礼,大伯母托人捎来的份子钱,用信封装着,连句节哀都没有。 "知道了。"我没接请柬,转身想回厨房,他却一把抓住我手腕,力道大得像铁钳:"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我是你长辈!" 手腕被捏得生疼,可心里那处更疼的地方却突然麻木了——原来在他眼里,"长辈"的权威比逝去的兄弟更重要。 "大伯,"我轻轻挣开他的手,指了指墙上父亲的遗像,"前年四月,我给您打了七个电话,您接一个,我今天就不会让您站在门外。" 他的脸"唰"地白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公文包上的金属扣在安静的屋里反光,像个嘲讽的句号。 后来他怎么走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本红请柬被遗落在鞋柜上,旁边是我早上没喝完的半杯豆浆,已经凉透了。 傍晚炒菜时,油烟机嗡嗡转着,我突然想:是不是所有亲近的关系,都要经过一次彻底的失望,才能看清真相? 现在我学会了,对不珍惜你的人,最狠的报复不是争吵,而是把他从你的世界里,轻轻划掉。 就像此刻,我把那本红请柬丢进垃圾桶,连带那些年的期待和委屈,一起倒掉了。 窗外的天慢慢暗下来,厨房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落在新买的绿萝上,叶子绿得发亮。
大伯有钱有势,今天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我一次也没有接,后来他又发了消息,我也装作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2-24 11:23:09
0
阅读: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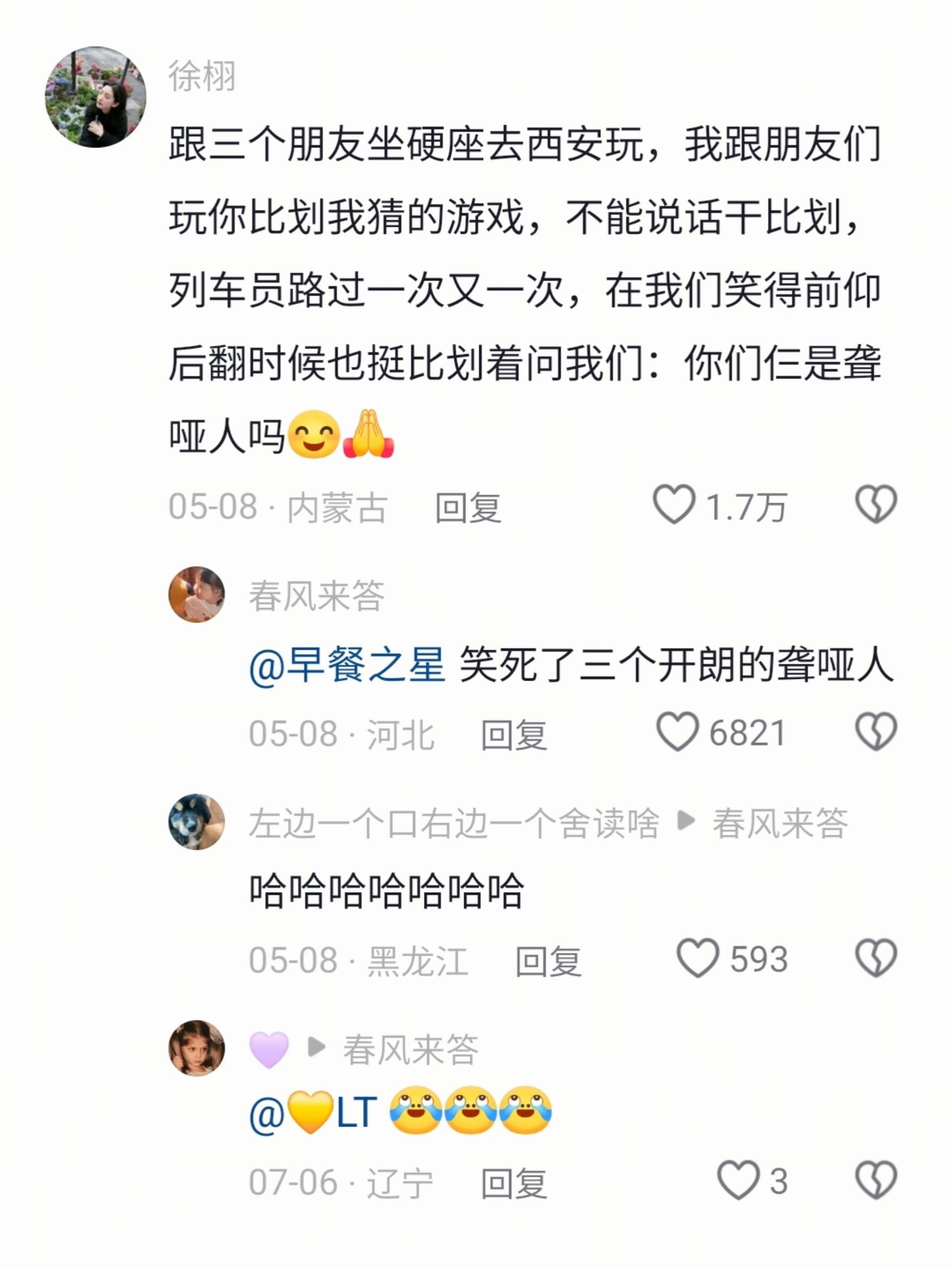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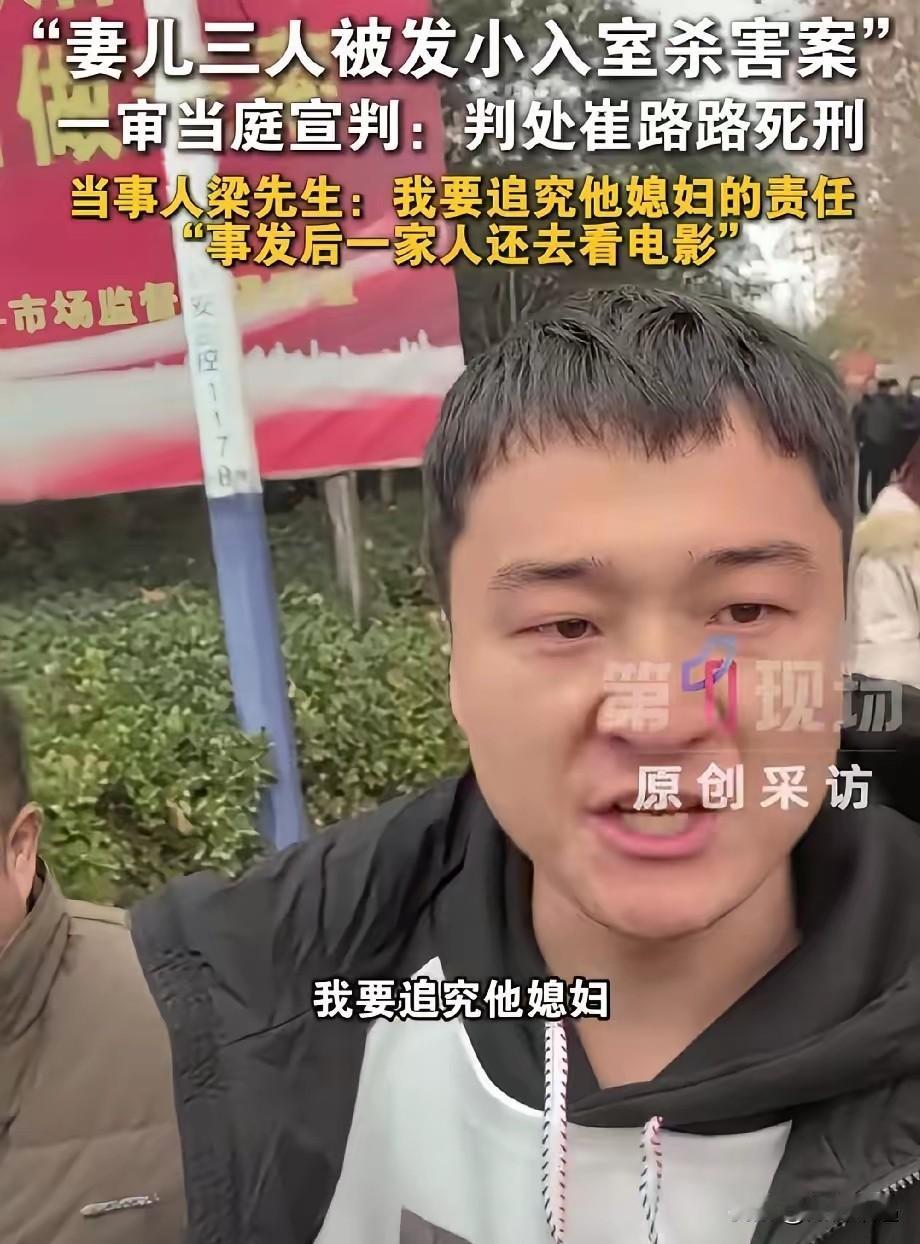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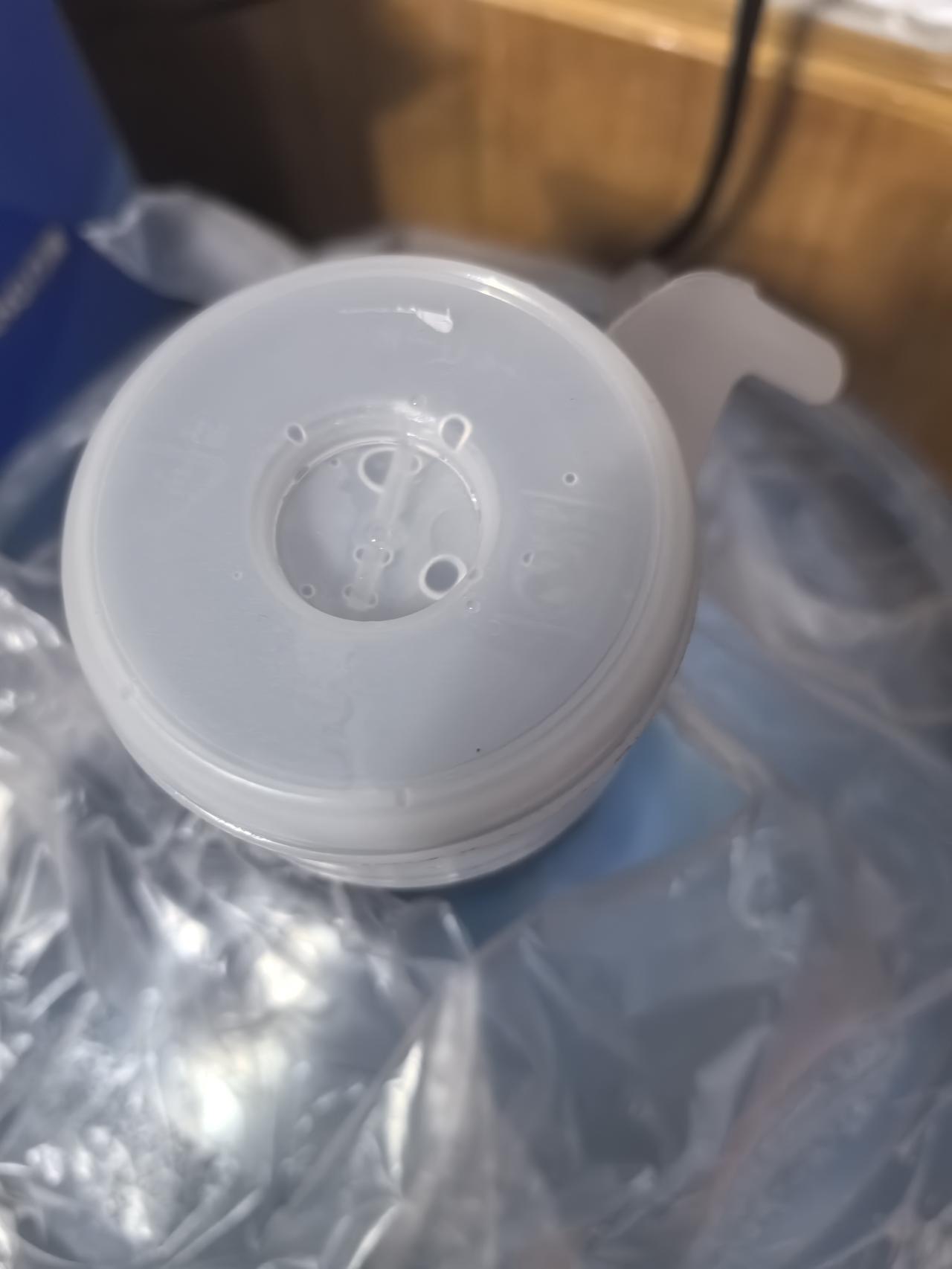


开心的弘儿
有骨气的侄子!这样的大伯等于没有,他对人不亲,又何必去亲他。
一锤定音
人家不差你那点钱,没准以后你还用得着人家,不要把路走太绝了
岁岁平安 回复 12-24 15:30
无事都不管,等真有事大伯能帮上忙?
用户10xxx54 回复 12-24 18:18
我看兄台脑回路清奇,有练无相神功的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