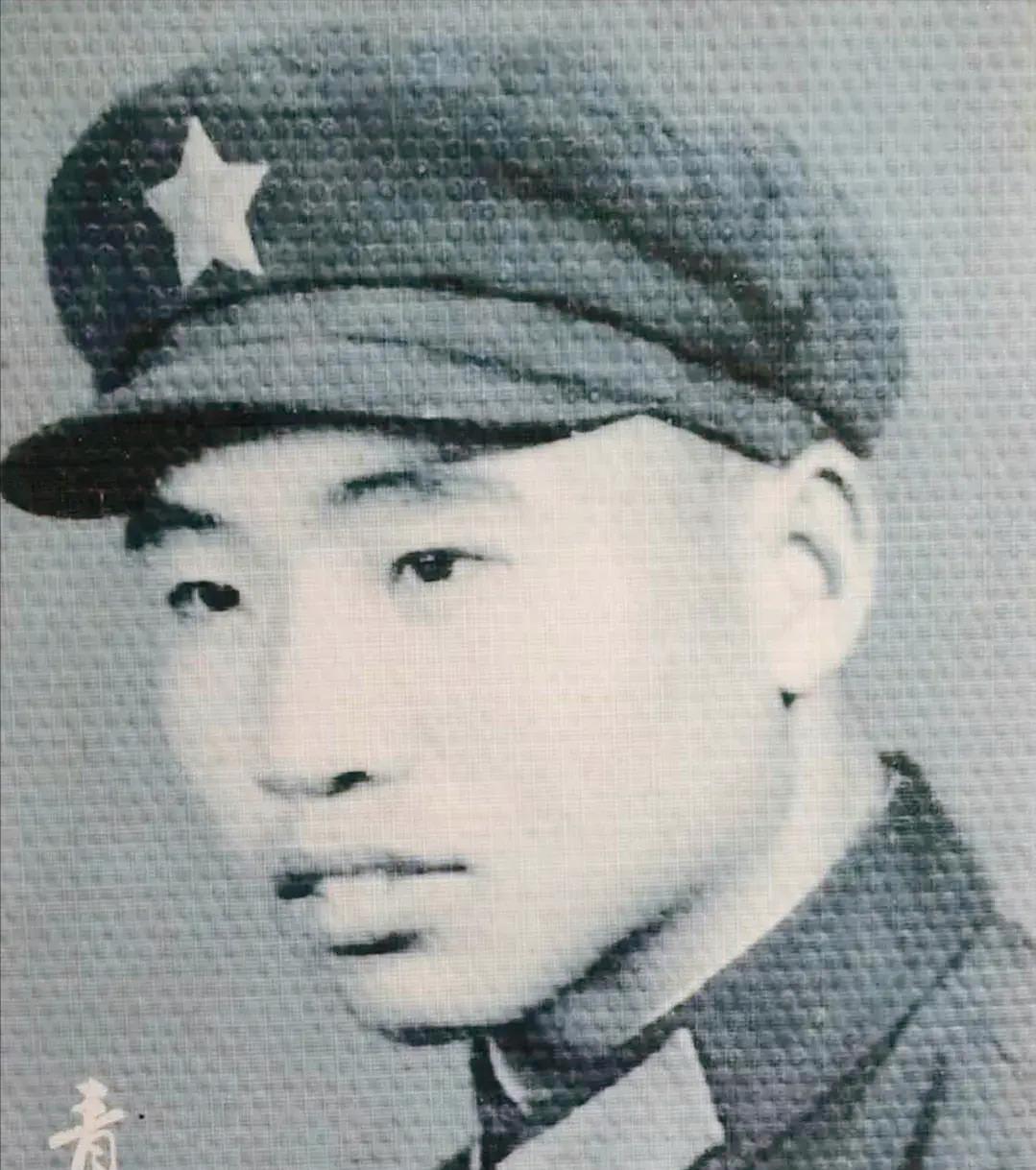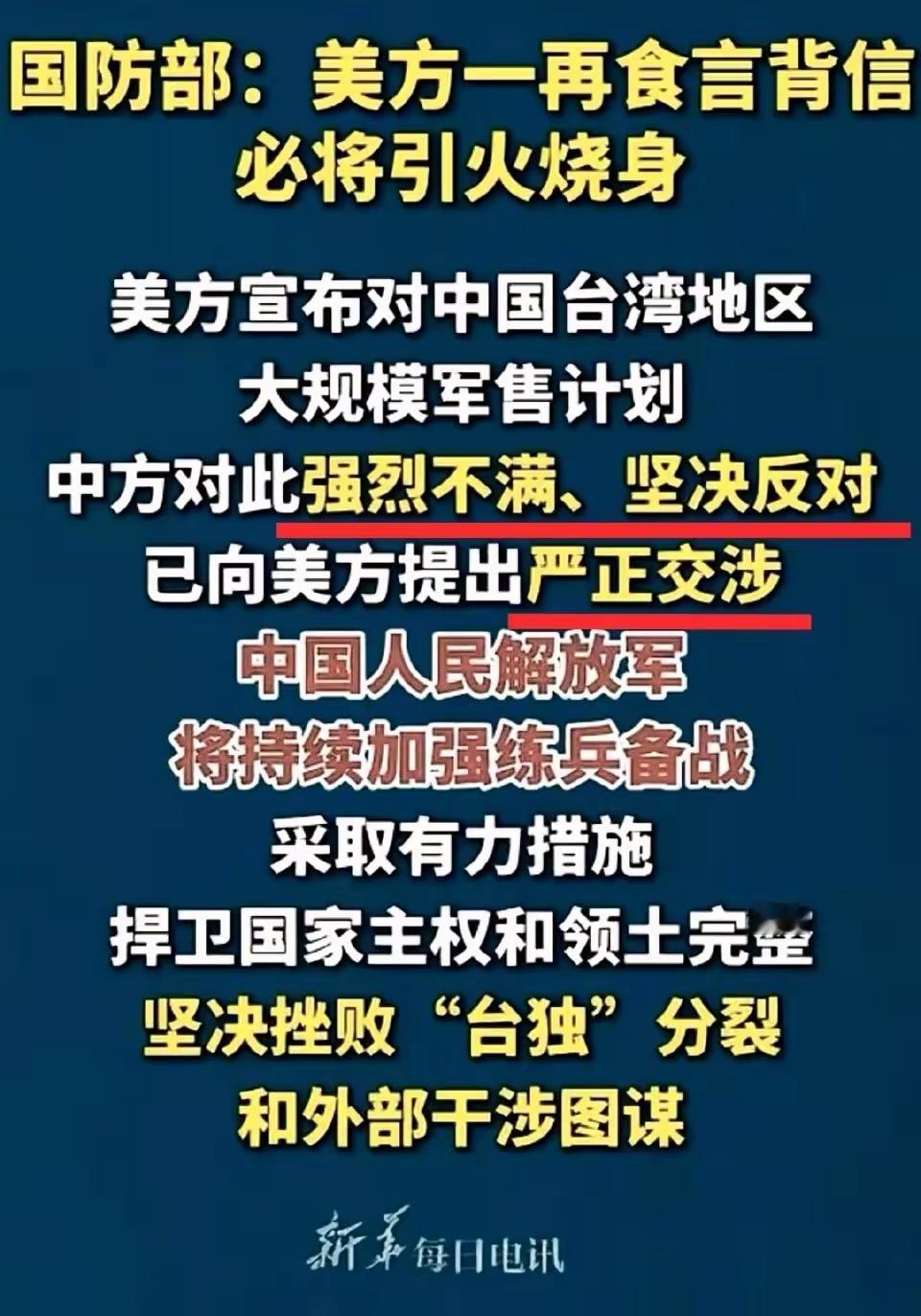1984年,一位身中100多个弹片的解放军战士,因抢救无效,被送往火葬场,就在战友们悲痛之时,“尸体”突然活了! 战士们用草绳捆着简易担架往火葬场走,雨水泥浆裹着担架腿直打滑。 第三次差点摔下来时,卫生员郑英突然抓住担架杆:“不对劲,他胸口还有热气!”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刚才还在低声啜泣的队伍瞬间停住脚步。 茅山阵地上的硝烟还没散,李陶雄趴在弹坑里已经没了动静。 高爆弹在三米外炸开时,他正给伤员包扎,170块弹片像冰雹似的砸进身体。 急救所里,医生摸不到脉搏,血压计指针纹丝不动,只能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字。 谁也没注意到,他涣散的瞳孔里还藏着一丝微光。 转运车在山路上颠簸,担架两次从车厢滑落。 郑英蹲下去想把遗体摆端正,手指却触到温热的皮肤。 她扯开染血的军装,看见胸腔微弱起伏,像风中残烛。 “快掉头!”她嘶吼着扑上去按住输液管,血袋顺着山壁滑进车厢,在颠簸中晃出暗红的涟漪。 2500毫升鲜血顺着橡胶管流进血管时,李陶雄的手指突然动了。 护士们举着马灯围过来,看见他干裂的嘴唇翕动着。 后来转到303医院,医生从他肝区取出枚指甲盖大的弹片,手术钳碰到时,监护仪突然发出尖锐的蜂鸣,心率跳到了52次。 昏迷两个月后,李陶雄睁开眼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郑英挂在床头的军功章。 那是他班长牺牲前塞给他的,弹片穿透胸膛时,这枚勋章帮他挡住了心脏要害。 “我们赢了吗?”他沙哑着问,手不自觉摸向胸口,那里还留着勋章压出的月牙形疤痕。 现在那枚军功章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玻璃展柜里放着张泛黄的输血记录单。 当年参与抢救的郑英已经退休,每次去参观都会在展柜前站很久。 她说总想起那个雨夜,草绳勒进手心的疼,还有血袋里晃动的光,像极了阵地上永不熄灭的信号弹。